《春秋》《国语》中的易占
不少人在问,先秦时期的人是如何看待《易》、使用《易》的?翻翻古书吧,比如《春秋》和《国语》,可以从中找到些线索。
1.
我翻了翻书,发现了好些个有意思的点,比如那时还没有爻题。
下面,我就当前一些发现和理解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吧。
(1)爻辞的引用
现在通行本《易》的每条爻辞前面都有初六、九二之类的爻题,这样我们想说某卦的某条爻辞直接报上爻题也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春秋》和《国语》中提到某条爻辞另有说法,即「某卦之某卦」。比如,里头用「乾之姤」指代乾卦初九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观察一下,不难发现,乾、姤两卦卦画只有第一爻不同。这样,借助姤卦,就把乾卦的初爻标识出来了。讲真,在没有爻题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清·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
在这,关于爻题多说几句吧。爻题,用六和九来指代爻性,即阴和阳;用初、二、三、四、五、上来指代爻位,即卦画由下而上的顺序;将爻性与爻位连缀起来就有了爻题,比如初六(阴爻,第一爻)、九二(阳爻,第二爻)。
感受一下,这是不是像极了有些家长称呼孩子大丫头、二小子?
至于爻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抵是战国中晚期,不会很早的!

(2)关于「八」
说到爻辞的引用,不得不提让很多学者伤透脑筋的「八」(《国语·晋语》:「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
©清·黄丕烈《国语韦昭注》
那么,「八」究竟何意呢?对此,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先秦用「八」(或「之八」)指卦画相反的卦,进而借此指代本卦卦辞(张意文、樊圣《<左传><国语>中的<周易>筮法》)。也就是说,乾卦卦辞可以用「乾之八」来表示。
换句话说,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认为,「八」指的就是本卦卦辞。
在这,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冒出来的是「八」不是「七」?因为,旧时,「八」有分别、相反之意(《说文解字》:「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外,乾、坤两卦有第七爻(即用爻)哦,轮也该轮到「八」了吧!
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乾卦完全可以用「乾之七」来标识用爻呢?
当然。不过,《春秋》记录乾卦用爻有些呆板,即「乾之坤」。
讲真,我看,后世爻题的设计多半正是受到了「八」的启发呢!
(3)当时的筮法
《春秋》和《国语》中记录了不少的筮例,但是压根没提筮法。
后人基于《易传》中的记录推演出不少筮法(《易传·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各有道理,都很有趣。
显然,随着筮具的发展,筮法少不了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
比如,商人用龟甲,周人用蓍草,后人用铜钱,筮法自然不同。
其实,抛掷铜钱六次就能起一卦(设定正阳反阴),极其高效。
在这,我们要明白的是,《春秋》《国语》中的筮法已湮灭了!
(4)当时的筮书
从《春秋》《国语》中的卜筮记录来看呢,当中提到的一些卦爻辞并不见于今本《易经》(《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很古怪。
这意味着,那个时候,市面上流行着与今本《易》不同的筮书。
由此,《周礼》提到《连山》《归藏》之类的筮书就不奇怪了。
(5)不可以占险
《春秋》《国语》中的易占是用来卜问吉凶、成败,以及决疑。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已经有人明确提出《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不能借鬼神的力量干不道德的事情!比如,谁谁谁想干偷鸡摸狗的事,事先占卜一下问个吉凶,古人认为是不可以的。
没错,古人已经开始尝试着对《易》的使用范围做一些限定了!
2.
在《春秋》《国语》中,《易》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用法,那就是直接引用当中的卦爻辞证事、证理,这像极了古人引用《诗》《书》中的文句。
比如,知庄子论彘子刚愎自用、违纪出师必败,便直接引用师之临(即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证明(《左传·宣公十二年》)。
相比卜筮,这是古人对《易》的价值进行了改造和升华,对不?
3.
瞧吧,在《春秋》《国语》中,人们对易占的态度是发展着的。
当中,最突出的就是,人们不断往神秘占筮中注入理性的因素。
声明:部分内容来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以上内容,并不代表易德轩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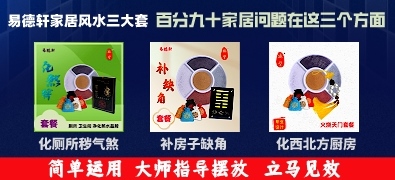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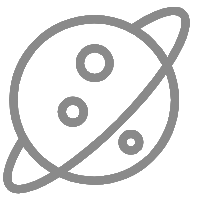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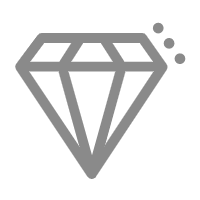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