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代表作
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奇怪的是本博主前天就有预感),让世界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无疑会给中国文学注入一剂强行针,可能会在不长时间内催生出具有超越时空影响的名著型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没有产生过世界性名著。十多年前,本博主做记者时曾经电话采访过莫言,其耿直爽快的山东汉子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在现实社会,许多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会向佛法吸取营养(很多本来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其应机教化世人,比如孔子就是红文殊的化身,后来还转世为司马迁,二者为构筑博大的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作家们也不例外,很多作家试图用文学的形式诠释六道轮回和佛法精髓,其中就包括莫言。莫言在接受诺贝尔奖组委会采访时特别推荐了他的长篇作品《生死疲劳》,莫言说:“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而这本书诠释的正是生命的六道轮回。下文综合转发自网络媒体。

中国本土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引言:
《生死疲劳》既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苦的书,又是一部关于 “六道轮回”的书——
莫言专访:《生死疲劳》从佛教思想出发(节选)
莫言透露,《生死疲劳》从“六道轮回”的佛教思想出发,主人公之一“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驴……”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
(南方日报记者 蒲荔子 2005年12月22日)
向佛经求源泉,莫言创作《生死疲劳》(节选)
东方早报记者 陈佳
据东方早报报道:莫言的每一部长篇似乎都有着某种突破性意义。3年前,一部《檀香刑》把莫言式的残忍和血腥发挥到了极至,而他下月即将推出的新长篇《生死疲劳》则以“轮回”的构架描画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12月12日,在接受早报专访时,莫言首次向媒体透露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历程与细节。
沉痛的血泪,不至血腥
不出意料,莫言的新作仍是农村题材,与以往的作品相比,甚至更具备某种史诗性。莫言透露,《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革命也是由土地革命开始。新中国以来我国的土地革命经历了互助组、人民公社,1980年之后又变为包产到户、小包干、大包干、分田到户,展现出由集中到再度恢复到分散的规律。”他说,农民饱经患难的历史,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螺旋上升的历史规律。
向佛经求源泉
“每一个作家都不希望重复自己,《生死疲劳》是我的一次探索。一次在承德参观庙宇时,偶然看到有关‘六道轮回’的文字,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莫言透露了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他介绍说,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阐释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另一个主人公即小说的叙述者,则在六道轮回中,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他所看到的故事。”
以“轮回”作为突破口
莫言说,书名《生死疲劳》也来自佛经中的一句:“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他说,佛教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摆脱令人痛苦的六道轮回,而人因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书名表面上与“土地”这个主题并无关联,但也深层次地探索着人与命运、人与历史的关系,“读者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尽管在创作中动用佛经资源,但莫言坦言对佛经没有任何研究,接触佛经纯粹是为了寻求创作上的突破。
《生死疲劳》由一个人在不同轮回中看到的片段构成乡村历史,有着零散的叙事结构。事实上,贾平凹和阿来2005年的新作《秦腔》、《空山》也是如此。评论家张颐武曾表示,中国乡村题材小说由完整性宏大叙事到破碎叙事的集体转型与中国乡村正走向消亡密切相关,莫言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出现这种转型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80年代以来中国完整性有关中国乡村的宏大叙事已经非常成功,很难超越,很多作家自然会转向在结构上有所突破。(记者:陈佳)
莫言接受诺奖组委会采访 推荐《生死疲劳》
2012年10月12日 09:02:51 来源: 京华时报
莫言推荐了今年在瑞典的出版的《生死疲劳》,“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原标题:莫言推荐《生死疲劳》)
在公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组委会立即用中文对莫言进行了电话采访,并将这长约8分钟的音频上传至官网。莫言表示,听到获奖后感到非常惊讶,会在今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包顿饺子庆祝。12月10日,他将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偏爱《生死疲劳》
在接受采访时,莫言表示,刚刚听到获奖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诺奖组委会说,全世界很多大学生会读他的作品,请他推荐一部。莫言推荐了今年在瑞典的出版的《生死疲劳》,“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他说,首先,这本书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土地农民问题的一种思考;其次在本书中,他采用了一种东方式的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此外,他在语言上也进行了探索试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该书初稿写作只用了43天时间,莫言说,这本书的创作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有这样一个农民,他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相对抗,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却显得非常极端和另类,被很多人打骂,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跟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分道扬镳,但他依然没有屈服。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后,觉得这个人物迟早会进入我的小说,所以这本小说写得非常快”。
和家人包饺子庆祝
谈到当年如何走上文学道路,莫言直言,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后来读得多了,就引发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当我拿起笔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有很多话要说,我发现通过文字表达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自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他坦言,当然他也想通过写作来证明自己、改变个人的命运。
对于庆祝方式,莫言连连笑言“没什么好庆祝的”。但他表示,晚上会跟家人一起包顿饺子吃,“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他说,12月10日,他一定会亲自前往瑞典领奖。(完)
人生本苦与生死幻灭——论莫言新作《生死疲劳》的佛教意识(节选)
张喜田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要: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体现了对佛教的慧悟。作家揭示了苦难永在、轮回不息、万物皆空的人生本相,这表明了他对人的本体性特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苦难虽然永在,但苦难又使人得以升华;轮回虽苦,也难以挣脱,但轮回表明了生命的永恒及众生平等;幻灭虽常常使人消沉,但也能使人胸怀大度、抵达至高境界。可见,莫言虽身陷红尘,但佛的慧根也不低于千年古刹里的世外高僧。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许多农村题材小说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描写农民在阶级压迫下遭受的苦难,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农村小说则改变了聚焦点,将视线推移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本身所带来的苦难,如《古船》、《白鹿原》、《缱绻与决绝》、《故乡天下黄花》和《丰乳肥臀》等。
……但是,其中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对人世与生命的感悟则是振聋发聩与发人深省的,而这种佛性着重体现在他对苦难、轮回与幻灭的叙述与证明上。
一、苦:人生本相。
根据佛教的教义,人生是大苦聚,苦是人生的真象。有情众生充满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恨苦、求不得苦和五盛蕴苦等。佛经屡屡提醒我们“人生是一大苦聚”、“一切皆苦”,这是佛教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看法,也是其对现实世界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受不尽的身心烦恼。此种烦恼,不仅是来自外在的环境,同时亦来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内心的种种欲望和烦恼,是苦所生的根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学的复兴与全球化浪潮中民族身份焦虑感的加重,很多中国作家向传统文化寻找滋养,而佛教的苦难意识在作品中呈现并日益加重无疑是文学向传统回归的标志之一。
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与地坛》,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均形象地揭示出“人生本苦”的生命底蕴,并把苦难当作本体意义上的生存境遇来表现。
《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也是以写苦难为主的。莫言带着一双佛眼去看待人生百态,得出“人生皆苦”的结论。……对他的转世的详细描写,不是为了歌颂他们的勤劳,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辛勤之苦痛、活着之危险……《生死疲劳》中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衣食住行)便充满痛苦。这种痛苦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早已出现,但从本体论上肯定生存之痛苦在我们的民族文学中则是不多见的。本体之苦的文化渊源不是儒道文化。而是佛教的底蕴。
在佛教看来,苦的根源是渴爱,即执著。由于众生的迷昧与执著,因而生起种种烦恼。众生有三种根本的烦恼,即贪、嗔、痴,此称为“三毒”,亦名日“三火”,而三毒均由执著而生。贪,是苦的直接原因。贪是对事物起爱著心,追求财物、美色、名声等而无厌足的精神作用。痴则更是痴迷执著。芸芸众生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渴求、欲望、贪婪、爱著,就是生起一切痛苦及使得生死相续不断的根源。渴爱不仅是对欲乐、财富、权势的贪求与执著,也包括了对意志理想、观点、意见、理论、概念、信仰等的贪求与执著。渴爱不足,苦海无边,回头无岸。
莫言在《生死疲劳》的题词中写道:“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而本书所体现的贪欲着重体现在爱财、色、欲上,具体说来,也就是爱土地、爱人、爱钱财、爱信念等。蓝脸、洪泰岳、西门金龙三人是“过于执”型的人物,他们的痛苦来源于“执著”。执著是坚贞,但何尝不是痴?痴是“三毒”、“三火”之一,同样是痛苦之根。蓝脸对个人单干的倔强、洪泰岳对集体经济的执拗、西门金龙对个人成就的渴望,均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在佛教中,六道轮回是为了破“执”,也可以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关于“执著”的颂歌和悲歌,人之所以苦就是因为“放不下”,但是,最终安放我们的只有这片土地,只有尘归尘、土归土,才能一了百了,涅槃寂灭,超脱痛苦。在《生死疲劳》中,人与牲畜的死亡是触目惊心的……
二、轮回:威慑与永恒
《生死疲劳》既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苦的书,又是一部关于 “六道轮回”的书。 轮回,指业的主体或生命在不同的存在领域中流转。在佛教看来,由于主体善恶业力的作用,众生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断流转、转生于六道,这六种转生的趋向是:天、人、畜牲、饿鬼、地狱、阿修罗——“天”最好,“阿修罗”最可怕。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一直在此三界六道之中生死相续,升堕不定,循环不已。如此生死相继、因果相依,便形成业报轮回。佛教认为,众生之来世究竟会轮回到哪一种类之中,完全是众生自身今世业行的结果。这便是因果报应,各自受报。
在《生死疲劳》中,作家对轮回的领悟表现在轮回之苦与报应思想上。西门闹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他为自己喊冤,他不断地经历着轮回,试图申冤昭雪,回归到人: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后又轮回到人。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但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在每道轮回中,他均有相应的动物性:“看看他脸上那些若隐若现的多种动物的表情,——驴的潇洒、牛的憨直与倔强、猪的贪婪与暴烈、狗的忠诚与谄媚、猴的机警与调皮。”
……这样,人常常处于对命运的不可知以及对轮回的畏惧之中。西门闹的轮回显示出了畜牲性,即处于畜牲道。这种动物性从传统的世俗眼光来看,有着等级观,畜牲与人是不平等的。随着业力的不同,果报也就不同,轮回的结果也不同。这也就表达了轮回的一种道德力量,人的所作所为,都会有报应的。
在中国民间,佛教的“轮回”观点是一股很强的道德制约力量。社会之所以还能比较安定,就是因为在老百姓的内心里有这样一种天然的自律:“恶人终得恶报,公道自在心中。”轮回的另一面就是因果报应。如西门闹对蓝脸有救命之恩,所以蓝脸对西门闹的子女与妻妾就有报答,他与西门闹的二姨太结婚,表面上是接收大员,其实是救她一命,并且把西门闹的一双儿女也救了下来。其实,轮回观背后还有一种“众生平等”观。六道轮回也表现了佛教的众生平等观。表面上看来,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牲有一个级别,从“天”到“畜牲”逐渐降低,但是背后他们是平等的。既然他们之间有轮回,也就证明不管自己的前世、今生是什么,他们也就不能因此世成“天”而自傲,也不因成“畜牲”而自卑,大家都是一样的,谁也确定不了前生是什么来世又会成为什么。更何况,佛教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如蓝脸所说:“老黑,我总觉得你是那头黑驴投胎转世,咱们两个有缘分呢。”
三、空:幻灭与升华
佛教在东土、在世俗人的眼中具有浓浓的出世思想。之所以出世,是因为看破红尘、幻灭过后而如此做。他们认为,万物皆为镜中花、水中月,一切皆空。“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并且,“空”因适应佛教人生归宿的学说即解脱论的需要而成为佛教哲学的第一个关键词。佛教认为,“缘起性空”与“无常为空”。事物是由各种因缘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存在一个主体或根本实体,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存在都以他物的存在为条件,没有完全绝对自立自在的东西。一切事物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因缘而生的。一切无常,无常为空。
莫言也许受民间文化的影响,把佛教之“空”常常理解为虚无,在《生死疲劳》中,表达了浓浓的幻灭感。《生死疲劳》描写了大量的死亡故事,这里既有人的死亡,也有动物的死亡,而这些死亡全是非正常的死亡,不是寿终正寝,而是突发事件造成的死,如西门闹、西门白氏、蓝脸、迎春、吴秋香、西门金龙、蓝脸、黄合作、庞抗美、庞春苗、庞凤凰、西门欢、黄开放、洪泰岳等;驴被饥民杀死、牛被金龙打死、狗自杀、猴被开放枪杀——真是一切无常,生命无常,生命最后化为乌有。不管身前多么荣华光耀,死神总会不期而至,死后便化为一杯黄土。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世必然会多次遇到生离死别,但是,作家突出地醒目地描写死亡,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死亡”便凸显出来,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生命是死,生命是空;生命本身就无存在的意义,一切也就化为虚无,幻灭感油然而生。
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经过驴、牛、猪、狗、猴、大头娃娃的六次轮回,仍没有解脱。在无穷的脱生中并没有挣脱轮回,难达寂灭,还需要继续轮回下去,这样,轮回似乎也成空。
佛教的“空”观对世俗的影响更多的也是最具有教化作用的是“戒欲”,不要贪欲与纵欲。欲是“三火”之一,最后要把人烧死。一切苦难与不幸缘于欲望,所以要戒欲,因为一切到头来全是空:权力为空、金钱为空、爱情为空、生命为空。一言以蔽之,欲望成空,一切欲望最后全化为空无。洪泰岳、西门金龙均成为革命的急先锋,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最后一块葬身火海。西门金龙在政治时髦时,成了政治的领军人物;在经济风行时,又成了大老板,女人、金钱、权力,他是一人独占,最后也只不过化为一块黑炭。洪泰岳一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参加地下党、锄汉奸、带头奔集体、与单干户斗争、与骗农坑农的人做斗争,一生为了自己的的本性,无欲无在——当欲望不存在时人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佛到最后也成为“空”的了;人只有感觉到生命的徒劳和徒劳的苍凉与悲怆! 莫言如此理解佛教及“空观”,表现出了他的佛教观的民间性与世俗性……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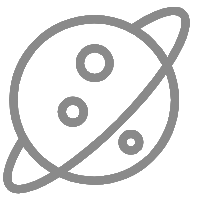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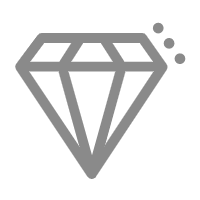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