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八大类
北京人过春节的习俗,是很有兴味的。所谓春节,是指中国阴历正月初一。它预示着新的开始,天地万物复苏,春天降临,一年的农事也将着手进行。所以,向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后来,公历推行,国家以公历的一月一日为“元旦”,阴历的“年喜”,只好在名义上退而求其次,改称“春节”。然而,对春节的庆祝,丝毫不因为名分的更改而稍减,依旧保持着传统的隆重,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族的盛典。而且,近几年又格外活跃,仿佛那曾经消失的典仪又活转来,在许多地方,过春节的热烈欢腾的气势,为近半个多世纪中所少见。只是“祭灶”的风俗还没有大规模恢复,甚至可能会从此不再恢复,人们已经从心底里冷淡或忘却了“灶君”(亦称“灶王爷”)这老爷子了。
“灶君”,就是“灶神”,据说是专司人间差恶的神。仿佛是情报机关派驻在每家每户的特别调察员。但他永久是副和善慈祥微笑可人的面孔,绝不怒目相向。这是否表现了中国人的某种由社会经验而来的观念,即察人阴私者往往总以微笑示人,并不作凶恶状以吓人呢?我不得而知,不过这总是很引人兴味的。“灶王爷”的尊姓大名,说法不一。《淮南子》上说:黄帝、炎帝“死作灶神”,职司人间善恶,足见中国人把灶王爷看得很重,他成了民族元始的化身。可是《五经异义》上说,灶王爷姓苏,名吉利,是我的同宗。我更宁愿相信这个说法,以便沾一份光荣。说起苏姓的先辈,除了四川的苏氏父子,三位大文人之外,还有一位人见人敬、历史悠久的灶王爷。灶王爷的后代,还不透着格外的自豪吗?而且,苏灶王爷还有位美貌的妻子,这便是“灶王奶奶”王搏颊。不幸的是,《酉阳杂记》跑出来打破我的这个光荣梦。它说灶王爷叫隗,貌若美女。还有的说法是灶王爷姓张名单,字子郭,他的夫人字卿忌。毫无疑问,我对这说法不感兴趣。可惜,民间习俗的势力是巨大的。我小时候就听见过民谣,说:“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柱香”人人会唱,坐定了灶王爷为张姓先辈的“错案”,让我失去了拣拾光荣衣钵的福分。老人们告诉我,说老北京市面儿上曾经有卖《灶王经》的,上面说:“灶王留下一卷经,念与善男信女听。我神姓张名自国,玉皇命我掌厨中。来到人间查善恶,未从做事我先清。”瞧那意思,灶王爷不仅铁定了姓张,而且是玉皇大帝的厨师长。被中国人的上帝指派到人间从事“查善恶”的特务活动。通俗是通俗了,可地位却大大降低,从炎黄的化身,一下子跌落为“上帝”的司务长,专干从锁孔里看人,从门缝听音儿的勾当。这就难怪中国人对这位老先生的态度有了更多的戏谑的成份。可我总不明白,玉皇大帝把自己的厨师长派到人间,他还开饭不开:难道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不管怎么说,灶王爷是位令人又敬又怕、又不能不应付的人物,不管他怎样笑嘻嘻。祭灶是古老的习俗,最早是称之为“纪灶”的。意思仿佛是纪念使人类最早用火而熟食的先灶者。可见,那时的灶君还没有沾染更多的神气儿。后来,他竟成了神,而且为上帝做饭,只是捎带手儿教会了人们炊事。原先的祭灶是夏天,到了后汉时代,有位叫阴子方的先生,在腊月(冬日)早上升火做饭,忽见灶神,在空中显形,说些什么,语焉不详,大约是抱怨伙食不好,肚子里荤腥不够。子方先生急忙将家中的狗(名曰“黄羊”)杀掉祭祀他。从此就家道兴盛,人财两旺。可见,灶王爷当了神仙就摆神仙架子,你不给我好吃的,我就不保佑你。于是,冬日杀狗祭灶神,就成了历代相传的风俗了。自然,这也是人们冬季打牙祭的好理由。供神人吃,久已有之。
还是近代人聪明,也会“偷工减料”,把祭灶的黄羊改为糖瓜,虽然甜蜜蜜,却永久地让灶君素食。祭灶日也定为腊月二十三日。因为,不知根据谁的考查,灶君必须在腊月二十四日赶赴天庭,到玉皇大帝面前报到,同时汇报人间的善恶。于是,人们在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为灶君送行。为了不让灶君说出自己的恶行。便供奉灶王以“糖瓜”“南糖”。这是一种用麦芽做成的糖,化后很粘。人们希望用这种甜蜜的封条粘住灶君的嘴,使他免开尊口。糊涂的人忘记了,坏话虽然不能出口;好话却也不能吐露。中国人大约信奉“无害即有益”的价值观,所以,实际上并不祈求神佛保佑,只求无害于自己,便宁愿奉上尊敬。

我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或北京人)关于天庭与人世距离的推测。既然灶王爷可以于一个夜间便飞升到天堂,好赶上凌晨的早朝。那么又为什么直到七天以后,在腊月三十除夕夜才又被请回来呢?灶王爷要么在天庭休假一周,要么就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要灶王先生七天打来回。不管怎么说,这七天的概念,同西方基督教一个礼拜的数目不谋而合,而且,这概念肯定还早于西方,足见中国人对于天文学的知识曾领先于世界,只不过带有迷信与世俗的色彩罢了。
倘从谑笑的推理上看,灶王先生的六天假期也不轻松。这是惶急的等待玉皇大帝接见的六天。玉皇陛下肯定不能同时接见几万、几万万个灶王,排队拿号坐等是必然的了。何况灶王爷一个个黑眉漆眼儿,嘴被粘住,说话呼呼噜噜,肯定不被玉皇老倌儿喜欢,说不定他老先生听得不耐烦,于第七天下午照本宣科地念一遍“去旧迎新诏书”,便挥挥手,让灶王爷们洗个澡,见见新,再重赴人间。可笑的是,明知这是个已经遭人间戏弄、业已变形的仪式,可人间、天上依旧每年装模作样的庄严地进行。没人打算捅破这久远的玩笑,在虚伪中耍弄欺瞒自己的主宰,获得内心的自我满足。所以,实在应当由国家颁布一个法令,规定每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为中国人的“愚神节”或“自愚节”,用各种仪式耍弄神仙,将自己心中的神圣和自我欺骗一齐扫荡殆净,换一个充满自信、相信自身的真正的新人。
中国人对神佛是相当宽厚的。只要是神,他的一切也都连带受到尊崇和祭祀。灶王既为一家之主,自然更觉亲切,所以灶君太太和他们跨下的坐骑,一并受到祭祀。不过,这种灶君夫妇及马的“神仙码儿”,(又称双座),只供家长夫妇双全的人家供奉。而丧失了配偶的人家,不管是鳏还是寡,则只供奉灶王爷,谓之单座。这不仅表现了男子汉夫权的神圣,而且也把“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的标准夫妻模式一并赠给灶君。由此可以窥见灶君其实是人造的,可以随人的意愿或是夫妇同行或是先生出差,夫人留守。一切看人的意思。人造了他或她,还煞有介事地奉迎,怎么看都透着滑稽。
这种灶君像,不论双座、单座,均为木刻板、水彩印刷,较为讲究。神像上方是当年的二十四节气,神像下有神驹,神像两旁印有对联,谓“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供奉者多系小户人家及农夫,其“宫”自然简陋,不过灶王爷及夫人总是安于职守,不像今天的官员还要挑拣岗位。灶王爷比现代的公务员可爱得多。
腊月二十三晚,这些在灶头吃够一年灶灰的灶王爷爷及奶奶,受到人们尊崇。供果虽极简单,仪式却极庄严。晚饭后,将室内各炉火升旺,全家聚会一处,在供桌上摆好关东糖、糖瓜、南糖三五碗,凉水一碗,草料一碟。(凉水及草秸、料豆是给灶君的马吃的,人们的想像及服务真是格外周全。)再摆好烛台,香炉等祭器。祭把开始,先点燃用羊油做的专供祭把用的小红烛。(此种红烛,旧时称之为“小双包”)蜡台下压着黄钱、千张、元宝敬神钱粮一至二份。由男家长主祭上香。北京民俗:“女不祭灶、男不拜月”。但我小时候,这个禁令已被打破,女人也祭灶,男人也拜月。只是祭灶时一般男先女后,依次三叩首,肃立十分钟,香烛欲尽,再次三叩首,然后把未燃毕的香根连同灶王码儿、钱粮、草料等一起放在院子里的“钱粮盆”(生铁铸成的大盆)中,和已经放在盆里的松枝、芝麻秸一起焚化。当盆中的火苗升腾起来时,主祭者还往往祝祷不断,说:“老灶王爷,您多说好话,少言坏语吧!”至於摆设的关东糖、糖瓜之类,则分一小块扔进盆中,去粘灶王的嘴,剩下的,悉数被人扔进自己的嘴里,所谓“上供人吃,心到神知”。神仙只是人们心愿中的一个符号罢了。
富商巨贾的祭灶自然与普通人不同。他们的供品不但丰盛,关东糖可以堆得如小山一样高,而且还要糊上八抬大轿,翻毛大马,马鞍一副。焚化升天后,全店的伙计在院中踩着铺满一地的芝麻秸。贫苦人家的灶王爷就没有这福分了,一碗凉水三柱香,三个叩首,谓之“磕素头”,把灶王码儿就地一烧,就算礼成了,灶王爷照样上天,也好伺候。
祭灶是春节将到的信号,北京人叫“过小年儿”。这一天后,各商号的伙计纷纷出外讨帐。自然,躲债者也不少,直到除夕接神(灶王)时,才不再讨旧账,所以又有“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包饺子”一说。
不管怎么说,灶王爷也是最接近民间的神祈,无论怎样地神气,毕竟保留着更多的凡人的精气神儿。所以,这位可亲可爱又常常受人愚弄的神,实在是人们发泄一年来郁积下的苦与甜的好对象。实在说,恨灶王爷者寡,逗灶王爷者众,这是位平民化的神仙。
近来看灶王爷的神像,总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他,我真希望灶王爷还是姓苏为好,恳求考据家们多多关照,完成这一“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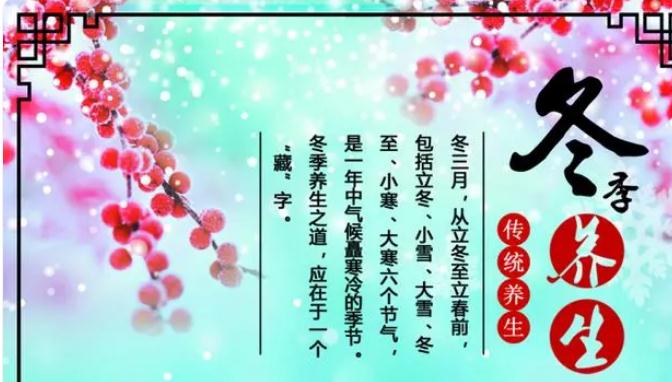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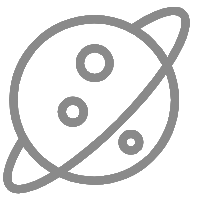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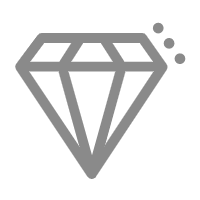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