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打扮的女孩称“貂婵” 趣说徽州话的民间味道
有时想,方言可能也会左右一个人的当下状态。当讲起徽州话,仿佛一下子就把自己从城市抛回乡村,从北方平原一览无余的寂寞抛回江南的梅子青青,抛回甜不甜涩不涩如枝头青桔的村姑模样。念多少书又如何,讲官话(老徽州人称普通话为“官话”)又如何,再像城市姑娘又如何,照样将你打回原汁原味,是火腿炖竹笋,是滋滋冒油的石头guo ,或者竟是野兔子肉的山野味道。没有什么比徽州话更让一个徽州人迅疾地回归徽州的民间味道了。这似乎比白墙黑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更经得起风吹雨打,抬望眼,方言的天井只落进徽州的雨水。
古徽州“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隔山隔水,“十里不同音”。同属歙县,东南西北四乡八里的话差别很大,还有的人家独居山顶或半山腰,他们的话比山下村镇的人说的更“山里”一些,有时也会招来白眼,不屑地说声“山里佬”。最有优越感的当然是城里人,乡下孩子背着米袋进城读书,首先要抖落“乡气”的就是话音,就像刚近视200度就急着买眼镜,先有个书生模样再说。如果谁戴了眼镜最后还是惶惶地回家种田,乡人会说:“文又文不得,武又武不得,上山斫柴再跌掉眼镜,那就好戏(有热闹看)了。”
去年回老家,编村志的老先生特意到我家,送给我一本。村志很朴素,封面的图片是村中的一道古巷口,上书“青田里”。青田不独自然,也有人文历史。我是出了阁的女儿,按理不当有此书。不过老先生说我是读书人,不一样。村志有一章曰“方言词汇”,看后如醍醐灌顶,很多疑惑也释然了。采撷如下:
小官:未成年男子。
外婆那一辈人保媒时夸男方俊,都说“是个好小官。”“小官”有些古韵,每每听到这个词,总会想到山路上挑着担子疾步而走的青壮男子,面白,发黑,寡言,稳实。绣楼上的小姐藏在格子木窗后看“小官”,山里人家的“妮”躲在锅灶后头听媒婆夸“小官”,不外乎都要找个好“小官”。外婆的娘家还在山里头,青山叠然,清泉泠然,当年也是看外公“小官”好(模样周正),才翻山越岭嫁过来。外婆比同村的姑娘嫁得远,难免后悔,因为受了委屈只有回娘家诉苦 ,她那双裹了又放的小脚得走高高低低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山一程,水一程,就为了那一哭。哭完了还得自个儿又走回去。当年外婆看我找个“小官”老老远(那么远),也很是不舍,怕我受委屈回娘家不易,哭都没地方去哭。不过我找的“小官”模样虽一般人却很好,外婆地下有知,可以一笑了。
貂婵:爱打扮的女孩。
民间女子当布衣荆钗不施粉黛,人前端庄人后也不聒噪,方是正道。若皆如此,乡村也没什么故事可传了。还是有那种女子,仿佛花蝴蝶投生,就爱花花草草。三分人材七分打扮,若生得个面白唇红(一白遮三丑),那就很“貂婵”了。说她“貂婵”,未必是夸赞,当然美是美的,只不过美得有些邪乎劲,一半的意思是不够稳重。从这点来看,倒貌似传说中的貂蝉了。
有户人家六个女儿,三女儿最“貂婵”,招惹了不少是非。她出嫁那天,村人都说这下安生了。这个女儿嫁到了县城附近的上海农场,那时上海知青很抢手,上海人,有工作,吃商品粮,那还了得。可惜她嫁的男人又矮又有点“痴”(脑子不很灵),“小官”不行,但有工作,是上海人,照嫁不误。后来听说生了个儿子,自己好歹也混了个临时工。但没几年农场倒闭,上海人退潮一样退回上海。她也随波逐流到了上海。后来那男人失业,她很明智地离了,再嫁了一个有钱的浙江人。浙江人的女儿都快出嫁了,那又怎样?反正回老家的时候穿金戴银,细皮嫩肉的。再后来听说又离了,那老男人打她。她又跟原来的男人复婚,在上海混着日子,反正能活着。她儿子也大了,脑子也不太好使,就学剃头。到外婆家来,也带着剃头箱子,免费为村人剃头,手艺不行,态度很好。
我一直很好奇也纳闷她的人生,不知那样的日子怎么过的。不过母亲告诉我,她偶尔回村,还是很心满意足的样子。婚姻是她的跳板,徽州牌坊的影子一点也投不到她身上。当然,母亲是绝不允许我这样“貂婵”的,我也学不会。
声明:部分内容来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以上内容,并不代表易德轩观点。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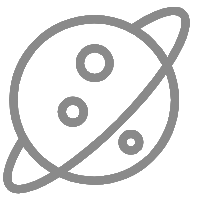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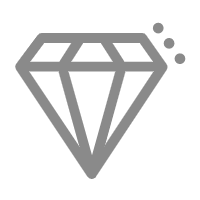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