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形而上之道”(8)
朱熹之所以要改造邵子《先天图》,以“加一倍法”出黑白块大小二横图,是出于建立其系统理学的需要。三画与六画之乾是由“一阳”的加一倍法单独生成;三画与六画之坤是由“一阴”的加一倍法单独生成,与邵雍“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说矛盾。朱熹之所以要改造周子的《太极图》,亦是出于建立其系统理学的需要。周子曰“自无极而为太极”,朱熹忌讳“无极”出于老庄,于是就改作“无极而太极”,并作“无形而有理”之解;周子所谓的“动静”是“太极”的动静,而朱熹则以太极为“一理”,理不会动静,于是就把周子的“动阳”、“静阴”改作“阳动”、“阴静”。朱子的“阳动”、“阴静”说就是以阴阳为物,而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之义。他说“才动便是阳,才静便是阴,未消别看,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此说无主语,不谓“太极”才动才静,是因其以“太极”为一理;他不同意《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于是就把周子的“分土王四季”改作五行相生。二程曰“理无形,因象以明理”,朱熹则主“有是理便有是气”、“理乘气”之说,理在气先,于是,明理就无须因象。“方其有阳,哪里知道有阴?有乾卦,哪里知道有坤卦?”(《朱子语类》),此则谓阴阳可以独立,而二程曰“阴阳消长之际,无截然断绝之理”、“静中变有动,动中自有静”、“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二程遗书》),显然,朱熹背离了二程之说。
《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与《老子》“道生一”说有合,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组织质变模式,朱熹则以“阴阳加一倍法”将其改造成为他组织的量变模式。“一阳”与“一阴”皆可无限地“一分为二”,无论分到什么时候,还是“一阳”与“一阴”,如何会有“万物化生”?“分”并不是“变化”,“分阴分阳”亦不是“阴阳不测”之“神”。又其“动力”由何处而来?“分”为谁之分耶?“理分阴阳”,如谓其皆自“太极”而分,则“一理”分为“万理”,终不出“理”之外,如何会有“万物化生”?。显然,其理学思想与《易传》相背离。
总而言之,自先秦诸子至南宋朱熹之“形而上之道”说,是一有本有源的学说,亦是一“一致而百虑”的学说。无论是“道家”或“儒家”,对于自组织的宇宙论都是共同认可的。只不过有人以之演绎得多有人以之演绎得少而已。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道说”或“理说”,皆不是“上帝创世说”。《易传·系辞》:“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谁能否定孔子不言“形而上之道”?一个学说的形成,必有其前因后果。即便是宋儒说“形而上之道”,亦不离老庄说之本源,只不过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发展与发挥罢了。托克托修《宋史》将邵雍、周敦颐等列入“道学传”,其对“道学”有见也。今有人谈中国古代哲学,必分“道家”与“儒家”之门户,愚见,就“形而上之道”言,起码北宋之前是“一门而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宇宙论方面,皆同归于自组织运动,虽有百虑而其目的地则一致而无二也。有如一株参天大树,虽千枝万叶,然其根则一也。此根乃自然发生之根,其神则自然格之神,非人格神所植之根也。
本文以“形而上之道”为说,可谓选了一个大题目。虽大题目总是要有人来说,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笔者说到此也该停下了。虽本文力图以中国古代哲学概念与命题为说,然既谓“概念”、“命题”云云,则又不免越界(实在是无可奈何!)本文汇集大量诸子言论而不多加评论,是因相信读者自会判断之。笔者只不过是把零散的珍珠穿成一串,下点工夫而已。能正本清源者,必先明本源之所在;能成长篇大论者,必依据充分资料之整理,此乃本文所以为之抛砖也。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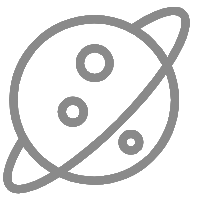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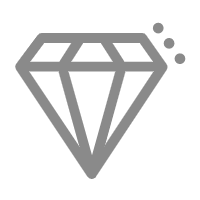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