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形而上之道”(7)
周敦颐《太极图易说》有“太极图”和“易说”组成。其《太极图》的模式是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而构建。“自无极而为太极”就是“道生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就是“一生二”,“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就是“二生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就是“三生万物”。语其始则道生太极,太极分而为天地,天地生五行,五行成万物;语其终则万物一五行,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道”为“虚无”之强名,“太极”为有,“无极”亦“道”之别名也。《易通》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在周子看来,“动静”乃是“太极”之动静,非“阳动”、“阴静”。又曰:“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万物乃“阳变阴合”而生成,非一分为二“一阳”或一分为二“一阴”而生成。其“神”之论:“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可谓“知变化之道,其知神之所为”者。《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易传》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周子立说皆本于此。“阴阳”为“形而下”者,“阳动”、“阴静”乃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之物,非“神”也。
张载《正蒙·太和篇第一》曰:“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申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氤氲,不足谓之太和。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容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虚空即气,则有五隐显,神化知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则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氲氲,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气聚得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灼也。其究一而已。……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对斯有象,对必反其为。”张子所谓之“太虚”是气散无形的状态,即“太虚”不是绝对的无。老氏“有生于无”之“无”亦不是“无无”,乃是“无形”之无。既赞庄生“野马”之说,则庄生与老氏不二也。《乾称篇第十七》曰: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耳。”张子谓“易无体”之类是“天易”,“易”之所以无体,是因其应机变化,则所谓“天易”与“太易”无区别。“指事而异名”亦不出“总而言之,皆虚无之谓”之外。其《易说·系辞》曰:“《系》之为言,或说易书,或说天,或说人,卒归一道,盖不异术。”又曰:“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卒归“形而上之道”,阴阳归太虚一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太虚”、“太和”之名,亦是“道”之别名。《易说·说卦》曰:“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一物两体者,气也。一故神,两故化。…两不立则一不可见。”此则不出“道生一,一生二”说之外。张子有“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之说,实则《系辞》曰“易有太极”则言太易有太极也。可知,其立说亦为不精。张子强调“为天地立心”并非完全本于《复》卦;强调“为往圣继绝学”,亦并非完全是“上承孔孟之志”。张子言“《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其于“道体”、“体用”方面的诸多突破,亦不是无本之木。所谓张载主“气一元论”说,只不过是他强调了“无物之物”而已。究其本源亦亦不出于老庄说之外。
《二程遗书》、《二程外书》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气,形而下者”、“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道,一本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既言气,则已是大段有形体之物”、“道则自然生万物”、“《老子》言甚杂,《阴符经》却不杂,然皆窥测天道之未尽者也”、“仁固是道,道却是总名”、“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老子亦言,三生万物,此是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儒者之入于圣人,理道皆一”等说,二程虽有“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之说,然其驳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是“以器言而非道”之“道”,乃是说“形而上之道”,可谓是知“道”者。天道、地道、人道、万物之道,皆为形而下之道,是器之道,非无形之道也。所谓“道非阴阳”,则亦是指“形而上之道”言。二程谓“气,形而下者”,就是不同意张载以“气散”为“太虚”之论。诚然,古代诸子论“道”,于“气”与“道”的关系方面似乎没有言明,但是“无无”一语已尽之。于“理”的方面,先秦诸子中有谓“一道万理”者,而二程“理、道皆一”之论,则是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所谓二程主“理一元论”说,是说他们把“形而上之道”中的一切概念皆归纳为“理”而已。“理”论乃“道”论,“理学”的根本就是“道学”。
虽然,北宋五子的宇宙论各有千秋,有人主“无极之前阴含阳”说;有人主“自无极而为太极”说;有人主“理、道皆一”说;有人主气散而为“太虚”说,但是,无一人不在言“气”。(以我们今天犹不可见之“空气”和可见之“水气”,可以推测古人“形而上”和“形而下”之思维。)只不过有人强调“形而下者”之有形之物,有人强调“形而上”之“无物之物”而已。以二程之学说看,既然“形而上”者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名,则诸多演绎而出之“无极”、“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大一”、“朴”、“神”、“玄”等命题,就可以“体、用、理”归纳之,至南宋朱熹就干脆突出了一个“理”字。无论如何演绎或归纳“形而上之道”,其本源都是出于《老子》之道。
南宋偏安于东南一隅,其时儒道门户之争空前激烈。朱熹可谓是建立儒家“形而上之道”说之集大成者。其学虽是源于二程,然又与二程有所不同。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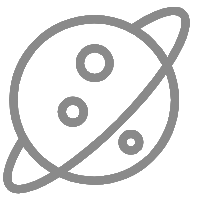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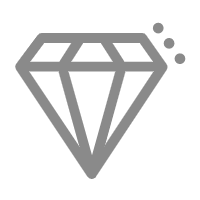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