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民俗现象
“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 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1967年至1968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1966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语文巫术
“文革”中的语文巫术,也是一类十分典型的民俗现象。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
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用特别的字体来表示。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1966年至1968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去抢救房屋和家里的财物,而首先拿起红宝书往外冲。报纸的评论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毛主席语录>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纸”之类的善良风俗。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朝阳大街”,“东方红广场”,“忠廷兵”,“左红兵”,“李反修”,“赵文革”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利用谐音漫骂,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吗?
中华思想
“文革”中曾有一种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经历了革命中心从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再到中国(毛泽东的时代)的转移。于是,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具备了特别的重要性。当时,人们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认为在帝修反的包围中,只要中国不倒,只要中国不变修,世界就有希望。林彪在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中,还将第三世界比喻为“世界的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将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
其实,这种说法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即“中华思想”。“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于象征性的照片,画面是在天安门前,有许多外国人围饶着毛泽东,它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此种理论里,世界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去拯救。所以,中国人不遗余力的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甚至自己勒紧裤带。在“文革”中,人们相信这种神话,完全忘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与“中华思想”相联系的,是“文革”对一切外来文化的拒绝。自19世纪后期以来,把西方或国外的一切文化通通视为妖术邪说的情形,屡屡见于一次又一次“土著”倾向的社会运动之中,如义和团运动等。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甚至在《山海经》的异民族观里,就有明确的体现;它只不过在“文革”中再次泛滥,表现的尤其典型而已。由于“中华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么盲目自大的要“领导”世界潮流,坚信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核心地位;要么自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以“光荣孤立”的形式与世界相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中,这两种倾向竟然相互纠和为一体,一方面自封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说世界革命的成败系于中国,另一方面又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自我隔绝而独走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之外。1973年的“蜗牛事件”,将美国公司赠送我方的玻璃蜗牛工艺品,视为对方侮辱我们“爬行”,进而大作文章。其实,蜗牛在美国象征着吉祥与幸福。
“中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一统的“天下观”。这在“文革”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例如,来自少数民族的颂歌风行一时;经过权力的重组之后,造反派的大联合,被说成是“从大乱到大治”;全国实现“一片红”,这只是走向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第一步;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方式,使意识形态实现绝对的统一。
二元对立的逻辑
“文革”曾批判过所谓“二元论”,但那是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政治和业务的两分法,恰好就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里的二元逻辑而成立的。类似的二元分类及其相互斗争,在“文革”中还有以下许多方面。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路线,香花与毒草,红与黑,好人与坏人,造反派与保皇派,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公与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众(外行)与专家(内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红与专,多数与少数,精神与物质,人与物(天,自然,武器),内与外,等等。这类两分法的逻辑,根源于中国民俗的思维方式,在“文革”中体现的尤其突出。
不过,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偏重,相反,它以价值偏重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价值偏重为一分为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价值偏重为兴无灭资;在左与右的冲突中,价值偏重为宁左勿右;在公与私之间,价值偏重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于物的矛盾里,价值偏重为人定胜天;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多数人(群众)的专政;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虽说又红又专,但价值偏重实际上为政治挂帅;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被认为不是个人享乐主义,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总是与封资修相关;在内与外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内,不仅强化内外有别,还总是把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归因于外部敌人的破坏。
“大同”与“千年王国”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旨在实现他的理想的运动。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大同”之梦和中国农民社会里与小生产相关联的“理想国”空想。
毛泽东用高工资,低就业的方法,初步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城市中均匀分享财富的问题,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方法,解决建国后的农民问题,实现天下公平与大同的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全国七万多个人民公社,经营了几十年,带来的却只有贫困。“共产风”的食堂大锅饭的破产,并未使他明白,他不仅坚持人民公社的实验,还进一步确定了继续革命的目标。
“文革”确实是从对于文化的革命开始的。1966年8月公布的“十六条”,把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视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道德,习俗与思想。但是,毛泽东擅长破坏一切现存世界的秩序,而不太擅长建立他头脑里构想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设想的新世界,基本上可用他在1968年5月7日发表的“五七”指示来说明,而且,他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乌托邦之中,进一步引入了新的内涵,即军事的乌托邦。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
首先,这是一个没有和反对社会分工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军人不仅要学军事,还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不仅要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办一些工厂,同时,还要参与地方的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不用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蒹学政治,军事与文化,并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蒹学军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蒹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实际上不承认社会分工,更不承认分工意味着进步。
其次,这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也许他认为,学校式的社会更有活力。在他看来,全国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毛泽东要求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进而希望全国都像解放军那样。在这个大学校里,人们相互学习,大家一起学习解放军,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学校里,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地位和用处,因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在其中没有多大用场。不用说,这是一个各方面包括制服与发型,都整齐划一的社会。
第三,这是一个只承认“道德人”,而不承认“生物人”的社会。雷锋,杰,愚公,张思德,白求恩,欧阳海,刘英俊,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不可攀。有许多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或者在临死时手中还要紧握语录本。一方面树立一个又一个高大而又辉煌的榜样,要求人们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则通过“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闪念”,甚至“群众运动”等触及灵魂的方式,来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社会,他甚至把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视为“私有财产”,从而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他要求清除一切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源,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说,这是一个贫富均匀,自力更生和知足常乐的社会。毛泽东想通过土地的国有,集体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来控制小农以及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显然,平均主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此种愿望,还把它当做十分有效的资源而充分的加以利用。回归“延安精神”,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价值,非常不幸,本来十分可贵的自力更生精神,却与关门主义结合了起来,使它几乎成了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的近义词。此外,
“忆苦思甜”不仅成为人们感恩戴德的表达方式,还成为告诫人民知足常乐,克制欲望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径。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欲望得到控制,而且不需要爱情,因为她属于“小资情调”,这一点多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
为了建立这样理想的“大同”社会,毛泽东采取了寻乎异常激进的途径和方式:让处于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拟青年毛泽东,大“闹”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权威挑战,捣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破坏一个旧世界”;让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改造与“再教育”;让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甚至还要他们来管理和改造大学,而且,这一切不必经过任何诸如考试之类的程序;让大,中,小学及所有教育部门,一概“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或干脆在工厂里开办“七二一”大学;让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让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去乡下为农民服务,进而在农村大力建设农民自己的医疗队伍即“赤脚医生”;在军队中取消军衔制,把军队建成“大学校”,并把全国建成军营,全民皆兵,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一概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让军队去“三支两军”,执行管制,宣传,和训练全社会的职能;让古人的(如春节)和洋人的一切“四旧”(封,资,修)统统见鬼,而代之以毛泽东思想。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按常理很难理解的怪事,例如,象小靳庄那样,“社会唱戏,请人种地”;考试答白卷者,照样可以上大学,等等。
事实表明,毛泽东的确破坏了他不喜欢的那个世界,但他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他所向往的“新”世界,因为,他的理想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实际上,毛泽东未能在破除“四旧”以后,具体地提供什么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旧”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说也是旧的。
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土著主义运动(千年王国运动)”的分析角度出发,可以说,“文革”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土著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例如,不论毛泽东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他都以“先知”,“导师”,“预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出现;在他身边或被他信任的人,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萨满或牧师的角色;运动以宗教狂热的方式展开;其指向虽说是与传统相决裂,但实际上,仍以回归“传统”为特点之一,这个“传统”不仅是“革命”的(长征和造反),而且,还是历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好和永恒的新世界,相信这个新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同和终极的意义(被中国的乡俗社会加以改造后的“共产主义”);绝对的排外和与外部世界的隔断及对立(反帝,反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等等。“文革”的确具有极端排外的性格,“洋奴”,“卖国贼”,“里通外国”的罪名,随时可以成立,与国外的任何联系,都可能是危险的。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人们有明显的危机感,“备战,备荒”,就是为了应付危机的。
根据有关“土著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社会的破产,固有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危机,外部世界的压力等,通常构成促发“土著主义运动”爆发的基本背景。回顾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传统面临艰难的转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面临进一步“中国化”的任务;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与苏联的反目,使中国陷入先是被孤立,然后是自我的“光荣”孤立等等,都对“文革”的发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热”
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了一阵引人注目的毛泽东“热”,于是,有人说,中国人再次发现了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被遗忘过。
在云南某地,曾出现过一个“幽灵中央”。人们相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死后都来到了当地某个村庄之旁,他们在冥冥之中经常召开会议,为当地老百姓排忧解难,据说还颇有些灵验。在西藏牧区,牧民的帐篷里始终把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啦嘛相并列。在陕西南部山区,人们为死者举行葬礼时,通常要播放《葬礼进行曲》,这首官定的曲子在1976年为毛泽东举行国葬时,为老百姓所熟悉,此后,便流传民间,成为礼乐化为礼俗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前来瞻仰遗容的队列,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在民间的口碑里,有许多关于毛泽东的神异传说,其中一则,说毛泽东警卫部队的番号8341,早就暗示了毛泽东能活83岁,能掌权41年。我的一位朋友以一篇题为《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的小说,获得了某刊物的一次全国大奖。
毛泽东去世后,给中国留下了权力和信仰的真空。当人们不得不反省“文革”的失误时,在感情上却宁愿把毛泽东和他身边那些推波助澜的人区别开来。有一个时期,周恩来成了人民移情的目标。
毛泽东生前的造神运动结束了,但他身后,又在民间开始了新的造神。他当然不必为他身后的造神负责。从中国民间信仰的特性来看,毛泽东的确可能成为乡俗社会诸神崇拜中新的一员。
在城市里,司机把毛泽东的画像,悬挂汽车的在驾驶室里,那不仅是一种时髦,还多少具有了安全护身符的性格。<红太阳>盒带的风行,唤起了一代人的怀旧情绪,“文革”可以被否定,但是,那曾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青春,热忱和梦幻,都与那个时代紧紧相联。不过,对<红太阳>用现代音响的技术,风格和意念加以处理,其效果已不再是殿堂里的颂歌,而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这也许再好不过地说明,眼下的毛泽东“热”,只是新的一轮社会流行现象,在城市,它是市民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农村,它是民间民俗与乡土文化的新内容。
新闻,出版,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有意或无意地渲染了毛泽东“热”,但他的形象却日渐少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日渐多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虽说在毛泽东“热”中,仍然多少有意识形态的走向隐藏其中,但其主流却是群众心理在市场经济面前的不安,以及对由毛泽东代表的那个平均主义社会和时代的留恋与怀念。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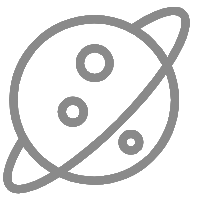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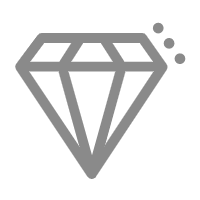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