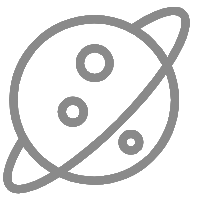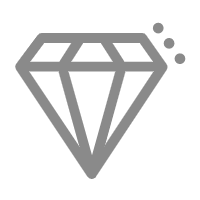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易经》与荣格的共时性理论
荣格临床期间著名例子:
“我举一个亲自经验到的例子。我治疗过一个年轻女孩,在治疗的关键期,她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人给她一只金甲虫。她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我坐在那里,背后是关着的窗户。突然我听到身后有些声响,像是轻轻的敲击声。我转过身去,发现一只小虫正在外面敲打窗玻璃。我打开窗户,在小虫飞进来的那一刻把它抓住了,原来是一只金龟子,这是在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上最像金甲虫的小昆虫了。此时,就在这一刻,它却一反常态,急着要飞进这黑暗的房间里来。我必须承认这类事情在这之前和之后从未发生在我身上,病人的那个梦在我的经历中仍然是如此独特。”
荣格在四十岁左右时接触《易经》,那正是其不惑之年。1920年11月荣格去德国达姆斯塔特参加“智慧学校”成立聚会,遇到从中国短期回国的卫礼贤,两人一见如故。荣格更是为卫礼贤所带来的“易经的智慧”深深吸引。

1921年12月15日,荣格邀请卫礼贤到瑞士苏黎世的“心理学俱乐部”讲学,主题便是中国的《易经》。在讲座期间,卫礼贤应荣格所求,现场演示了《易经》的占卜程序(50根蓍草的大衍之数)。
后来,荣格在纪念卫礼贤的时候,这样回顾往事:
“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研讨小组作第一次演讲时,应我的请求,他演示了利用《易经》占卜的方法,同时做了一项预言,这个预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准确无误地应验了。”
卫礼贤及其所翻译的《易经》,对荣格来说意义深远。荣格不仅熟读《易经》,而且反复研习易经的起卦与“占卜”。
在其自传中,荣格提到:
“大概在1920年,我开始对《易经》一书作实验。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心向这本谜一样的著作发起全面进攻。传统方法要求使用蓍草茎干,而我用一把芦苇代替。我常常在那棵百岁梨树下面的空地上一坐数小时,身旁摊着《易经》来练习卜筮,查阅那些环环相扣的谕示,看因果相互影响。各种各样确凿的神迹出现了——它们与我的思维过程形成有意义的联系,我自己都找不到解释。”
1925年,荣格与朋友一起去非洲旅行。由于感觉旅途具有风险,诸多不确定因素,荣格起卦求问《易经》,得“渐卦”,其九三爻有“夫征不復”之语,使得荣格颇为惦记,甚至预感此行所需付出的代价,甚至可能是生命的代价。
整个旅途中确实险象环生,有几位与其同船航行的旅客因感染相继死去,包括一位曾坐在他对面一起用餐的小伙子,荣格自己也生病,遭遇野兽袭击。然而,《易经》之“渐”的意象,对荣格深有启发与教诲。他将其旅行视为无意识的探险,谨守渐卦之“漸,女歸吉,利貞。”以及其象之启迪:“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安然完成其心满意足的非洲之旅。
1930年,在“纪念卫礼贤”的祭奠仪式演讲中,荣格说:
“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中国其他的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他继续说道:
“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这种观点目前正处在巨变之中,康德《纯粹理性批评》无法完成的任务,当代的物理学正求完成。因果律公理已从根本处动摇。我们现在了解我们所说的自然律,只是统计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会有例外发生。我们还没有充分体认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象……”
有关的反思,以及面对探索心理和心灵,意识和无意识之本质的需要,促使荣格关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易经》中所包含的“共时性”思想。
荣格曾坦言,尽管自己对有关“共时性”的思考由来已久,但一直缺乏足够的勇气将其公之于众。认真面对“共时性”现象十分困难,这与他长期的科学训练有着很大的冲突。
他说:
“共时性问题困惑我很长时间了,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
在《分析心理学论文集》第一版的前言中,荣格曾经提到:
“因果只是一种原则,并不能够穷尽一切心理现象。因为心灵(心理)是有目的的。”
他认为,心灵最终依赖于“先在的”意义,只有在是无意识的时候,才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假设在所有意识产生之前,存在一种“知识”。
随着荣格在无意识领域探索的深入,在其集体无意识的框架中对原型和象征的研究,尤其是研习了《易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和启迪之后,他始获得表达“共时性”的勇气和智慧。
荣格认为,共时性原则假设有种意义是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而且是独立于人而存在。这种形式的存在只能是先验的,因为它包含在从心理上看是相对的时间和空间中。也就是说,包含在不可表象的时空连续统(space-time continuum)中,就像关于未来的事件或空间上遥远的事件的知识所表明的那样。
在《易经》序言中,荣格说:
“正如因果性描述了事件的序列,对于中国心灵来说,共时性则关乎事件的同时发生。因果观告诉我们D是如何出现的这样一个戏剧性故事:它来自于在D之前的C,而C则来自其父B,如此等等。相形之下,共时性的观点则尝试产生一种同时发生均含有意义的图景,ABCD等如何同时同处共同出现呢?首先,因为物理事件A和B与心理事件C和D具备同样的性质;其次,它们都是同一情境中的组成因素。此情境表现为一种适当合理的图景。”
荣格认为,“共时性”现象可归纳为三类:
1. 观察者的心理状态和外在的客观时间即时相合(比如那只金龟子的例子)。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在事件和内在的心理状态有因果关系,而且由于时空的心理相对性,这种联系甚至是不可设想的。
2. 心理状态和发生在观察者的知觉领域之外(空间距离)的外在事件相对应,外在事件只是在随后才得到证实。
3. 心理状态和还不存在的未来事件相对应,未来事件由于时间距离,只能在随后才能得到证实。
荣格认为,在第2和第3点中,巧合的事件不处在观察者的知觉领域之内,而是被预期的,因而只能在后来被证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把这类事件叫做有共时性的事件,而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
由共时性现象,促使荣格关注“直觉方法”(intuitive method),即领悟整体情景的方法。荣格认为,“不像受希腊思想影响的西方人,中国人不是要看细节,而是将细节看作整体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不同于西方的因果分析,在《易经》中,凸显中国人的整体情境领悟。它将细节置于宇宙背景,以阴阳互动作为分析。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实验基础。
在“共时性:非因果关系原则”中,荣格说:
“我们一定要记住,西方的理性态度不是唯一可能的态度,并不能包含一切。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偏见。中国古老文明在这个方面总与我们不同,我们要在自己的文明中找到与此类似的东西,就要回到赫拉克利特的时代,至少在哲学上是如此。”
荣格认为,共时性并不比物理学的非连续性更神秘或更令人困惑。只是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因果律是绝对的,所以才觉得共时性现象是不可理解的,才不相信没有原因的事件会存在,或者会发生。
为了阐释“共时性”的意义,荣格提出了一个模型图,如图所示:
在荣格勾画其共时性原理的时候,不仅有泡利的参与,也有爱因斯坦的帮助。
荣格说:
“爱因斯坦教授有几次来我家做客,一起晚餐……这是爱因斯坦发展其相对论的早期。他试图将其相对论思想灌输给我们……正是他最初启发我思考时间和空间相对性,及其心理的制约性。30多年以后,有关思考使我与物理学家泡利教授一起来论证心理的共时性。”
由于爱因斯坦和泡利,荣格相信共时性与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泡利,以及泡利的良师益友玻尔(Niels Bohr),也都从中国与东方文化,尤其是《易经》中获益。
尽管有历史的反思和爱因斯坦与泡利的支持,在因果决定论盛行的时代,荣格所提出的“共时性”,可谓标新立异,惊世骇俗。
实际上,我们一直很好奇,作为中国文化众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到底对荣格说了什么?比如黑塞,将《易经》及中国文化融入其文学创造;比如泡利,将《易经》及中国文化,整合于其物理学研究体系。
荣格在其《回忆·梦·思考》中说:
“如何把握对立之整合,将我引向中国之道……惟有在我所思与研究到达关键之点,也即触及自性时,我才找到重返世界的归路。”
在荣格看来,通过中国的《易经》,“卫礼贤已为我们接种中国精神的生命胚基,这将使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根本变化。我们将不再沦落为临渊羡鱼或品头论足的旁观者,我们已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并能够体验到《易经》的生命活力。”
本文节选自《荣格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第三章“荣格与易经”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