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程子、朱子、吕子,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来,吕子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来底”等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及其崇奉,心悦诚服,如何又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的人呢?且如为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钻刺而得的道理。何况,这做圣贤也可以钻刺打点得么?且吕留良系一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如何尊敬悦服之诚,一至于此?今曾静还是尊敬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抑忿恨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务将心上实话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以吕留良为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用来的者,是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下见得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粹美,浑然无一毫圭角,令人摹拟得,是天生下来德器就如此纯全,人学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样,他是个荫补世袭官,生下来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资未甚高,生质亦未甚美,然他从持敬致知,循循做法,由下学而直造上达,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程颢、朱熹、吕留良,如同现在的人做官一样,程颢是世袭荫补祖上功德出身,朱熹是通过科甲举试及第,吕留良是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等言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极其崇拜敬奉,心悦诚服,为何又说他是街市江湖钻营的人呢?并且,担任官职也没有街市江湖中的下人可以钻营而做得的道理,何况这为人师表的人也可以钻营打点的么?再说吕留良如果是一个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之诚心到如此地步?如今曾静是尊敬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还是忿恨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务必要将心中实话招供出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将吕留良说成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人,只是一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中觉得程颢先生天资纯和,品德完美,浑然不露一丝一毫圭角而令人模仿得到,是天生下来德行器量就如此纯全的圣贤,人们是不能学他的,恰好他又像是做官的样子。他担任这个靠祖上功德而荫补世袭的官职,是他生下来就要由自己受用的。朱熹先生天赋不是很高,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然而他从小便抱着谨言慎行、敬奉师长的态度去学习知识,循序渐进,由虚心向人请教开始而达到了对义理透彻的了解,今日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令人可敬可学。恰如像做官的,是由科举正路出来的,靠自己辛苦读书得来的正果,人人都可以像他那样学得来。至于吕留良,观看他文字所记写的生平,少年本就不是个正经的学子,虚心求教学问的功夫,并不能拿得起来,而是剽东掠西,没有他不揽的事。到了中年之后只是专心写些评论文章,因撰写评论文章遂即得以了解程朱理学的精髓。所以当时说他是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也是说他本来没有问临政事、治理百姓的本领,只是办理闲杂事务得当,效力使用有功,朝廷怜悯他劳苦,也授予个闲杂的官职让他担任。这虽是当时轻率随意推崇他的话,其实也是自己心中天理发现,对他大有不满的表示。可惜当时没有人能指出他的言论观点的过失之处,并且也未曾看到过他的遗稿残编中有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言论,所以终于陷于他的迷惑之中。这都是由于自己学识见闻浅陋,看不破他的虚伪,而当时的学人文士又多认为他是写作文章的宗师,群起向他表示敬慕。所以我这山野鄙夫无知到极点,被他所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今日如不是恭逢皇上圣德齐天,洞察获悉我犯罪的事由,怜悯体念我陷罪的无知,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被磔尸碎骨,灭门抄族,也都是因为吕留良这个叛逆首凶毒害所造成的。今日假使吕留良还在世,我一定要吃他的肉,裹他的皮,以报深仇,岂止只是忿恨而已!这是发自我心腹的实话。天地明鉴在这里,如何能欺骗蒙蔽得过呢?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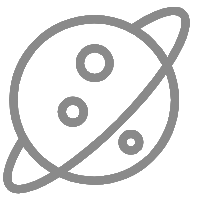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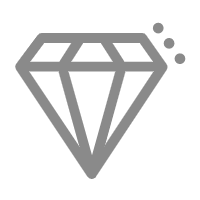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