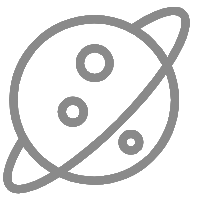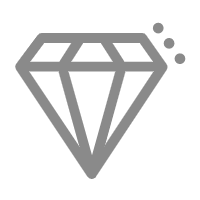易家论易--朱子易学学述
赵建功
内容提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朱子易学进行了探索:一.朱子强调,《易》本卜筮之书,但又不止于卜筮,故治《易》须兼重象数与义理,而不可有所偏废,阐发义理须以象数为基础,研究象数又须以义理为目的;二.他指出,《易》之为用,无所不该,因《易》是个空的物事,故治《易》不可拘执一物一理,而应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三.他主张,应严格区分《易经》、《易传》和易学,同时充分肯定各家的独特价值,故治《易》应摒弃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四.他提出,一物各具一太极,圣人是己与天为一,从而建立了自己独步千古的形上学,表现了深邃独到的终极关怀。
朱子思想博大精深,平实恢宏,综罗百代,影响广远。史称朱子“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②]钱穆先生曾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③]
然而,八百多年的盲目推崇、歪曲利用和感性抨击,极大地扭曲了真朱子。这就使我们很难平和公允地理解朱子。尽管如此,面对朱子这样一位卓立乾坤的思想巨人,面对其丰赡精湛的思想财富,又有谁能保持无愧的沉默?
朱子易学更是融贯古今,颇多创新,简易明达,卓尔不群,且能随缘点化,因宜生发,而有其不可替代的现代意义。本文即试图以一种力求平允的为学态度,对朱子的易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作一初步探索。
一.《易》本卜筮之书
朱子一生精研《周易》经传,熟谙易学历史及其进展。他对易学界极为普遍的那种偏执象数或义理的治《易》态度颇为不满,批评象数学派“滞泥而不通”,义理学派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④],都没有把握到《周易》的“本义”。他明确指出:
《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⑤]
近世学者颇喜说《易》……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⑥]
“谓易是卜筮书,最为大胆创论”[⑦],“可以说是企图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不仅对当时的义理学派,对象数学派的《周易》观也是一大冲击,在经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⑧]由此可见朱子易学的大胆创新、卓尔不群之处。
《周易》最初本是卜筮之书,但它却不仅仅是卜筮之书,而是统治阶级用以“神道设教”[⑨]、“教人为善”[⑩]的特殊典籍。然而,孔子之后的易学家几乎都不能充分认识或正视这一点,因此也就无法采取一种较为正确、合理的治《易》态度:他们或是以为《周易》“止于卜筮”,成为偏执象数的象数学派;或是只以《周易》“为理,而不以为卜筮”,或讳言《周易》为卜筮之书,成为偏执义理的义理学派。因此,朱子能破除一千多年的历史迷雾,大胆指出“《易》本卜筮之书”,但又不“止于卜筮”,显示了深厚的易学功底和超凡的易学卓识。
朱子对象数学派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其“苛细缴绕,令人厌听”[11],“太走作”,“附会穿凿”,许多说法令人“好笑”;即使偶有所得,“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极力”[12],以求必得之哉?他说:
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13]
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说阴阳,说阳便及阴,说阴便及阳,乾可为坤,坤可为乾,太走作。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体,一卦可变作八卦,也是好笑。[14]
然而,对于同样属于象数学派的邵雍,朱子虽然也批评他有些地方“大概近于附会穿凿”[15],解《易》时又“尽归之数”,但却在更多时候对他褒扬有加,说他“心地虚明,所以推得天地万物之理” ,说“康节先天后天之说最为有功”,对程颐有便利条件请教他“却轻之不问”深感不解和遗憾[16],说《周易·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然古今未见有识之者。至康节先生,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17],说“某看康节易了,都看别人底不得”[18]。同时,朱子吸取了邵子易学的许多成果,以致南宋学者魏了翁说,“朱文公易得于邵子为多,盖不读邵易,则茫不知《启蒙》《本义》之所以作。”[19]可见,朱子治学持论皆极平允,而绝无个人偏见杂入学术。这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朱子更对义理学派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们中的有些人,如主张“得意忘象”的王弼,提出“假象显义”的程颐,虽然有功于“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20],但是,他们在解《易》时“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21],则甚为不妥。他说:
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词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22]
朱子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故其词必根于象数”,“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用处之实”,若摒弃阔略卜筮、象数,则事无实证,而虚理易差,“却恐不见制作纲领、语意来历”[23]。如此,治《易》便如“画鬼神”[24],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解释《周易》,遂使《周易》不成其为《周易》,易学不成其为易学,则易学休矣。
因此,朱子进而尖锐地质问偏执义理的易学家:
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且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晓?又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 [25]
面对这种势不可挡的锐敏质问,那些偏执义理的易学家能作何回应?他们是否还能坚守立场而无动于衷?
朱子对义理学派的批评,甚至不回避他一向特别敬重的程颐。他认为,程颐虽“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其《易传》尽管“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只是于本义不相合。”[26]他批评道:
若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27]
但是,朱子在批评程颐易学不足的同时,仍然对其作出了极高评价,认为程氏《易传》是“因时立教,以承三圣”的哲学精品,只是“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乃磨砻工夫”[28],不宜初学《易》者看,而宜于有相当基础者细心体察,深契冥赏精微玄妙之易理。这种平和公允的治学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令人不胜敬慕。他说:
《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是岂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异,故其所以为教为法不得不异,而道则未尝不同也。然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惟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29]
“庖羲氏”即伏羲,“道则未尝不同”即“四圣一心”[30]。朱子有时说“三圣”,指上古伏羲、中古文王、近古孔子,有时说“四圣”,即三圣加上周公。盖因文王、周公同在近古,同是系辞,只是文王系卦辞,周公系爻辞,故他常常文王、周公连称,而三圣、四圣皆是传统说法,不必深究。朱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应严格区分《易经》、《易传》和各家易学,并充分肯定其各自价值(详见下文)。
在这里,朱子显示了自己明确的治《易》立场,他“既批评了汉易的象数之学,又批评了王弼派的玄学易学,而以程氏易学为正宗。据此,朱熹的易学,对筮法的解释,虽然吸收了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先天易学,但仍属于义理学派;或者说,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吸收象数学派的某些观点,以补其不足。”[31]
朱子撰写《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就是为了纠正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偏执。他认为,“《易》于六经,最为难读。穿穴太深,附会太巧,恐转失本指”[32],“经文本义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鄙说正为欲救此弊。”[33]因此,他吸取了两派解《易》的历史教训,采取了“简易”的治《易》风格,于不可下手处宁可付诸阙如,以为如此解《易》,则不至于有太大差谬。他在自述其撰述原委时说:
《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34]
近又尝作一小卜筮书……盖缘近世说《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不可研诘。故推本圣人经传中说象数者,只此数条,以意推之,以为是足以上究圣人作《易》之本指,下济生人观变玩占之实用。学《易》者决不可以不知。而凡说象数之过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矣。[35]
“小卜筮书”指《易学启蒙》,“此数条”指《易学启蒙》的“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四篇。朱子说,绝大多数易学家“好自用己意,解得不是”[36],“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于《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皆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37]由此可见,朱子对自己的学《易》心得颇为自信,自认为能纠正义理学派空寂虚谈和象数学派穿凿附会的偏颇,并融通各家易学的优长。他曾说,自己治《易》,“偶幸及此,私窃自庆,以为天启其衷。”[38]
朱子强烈反对那种舍弃卜筮而空谈义理的治《易》态度。他认为,虽然《易经》蕴含宇宙万物之大道玄理,等待我们去发掘和揭示,但是,我们须首先明白,《易经》本是卜筮之书,因此,阐发义理须以象数为基础,研究象数又须以义理为目的,治《易》须兼重象数与义理,而不可有所偏废。这种平允的治《易》态度,在偏执频见的易学史上极为可贵。朱伯崑先生就此指出:“这种对待《周易》的态度,表明朱熹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从而使他对《周易》经传的研究超过了前人的贡献。”[39]
在朱子的著述中,对象数、卜筮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易学启蒙》、《蓍卦考误》、《筮仪》、《易五赞》、《易象说》等就不用说了,即在《周易本义》中,也是首列九个易图(易图即非原有,也与《易学启蒙》基本一致),而在注经时更以象数为基础,认为解《易》时“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透”[40],这样才能达到《周易》之“本义”。这可能会使人感觉有过分推尊象数之嫌,然在朱子则自有一番道理。
今人李仕澂先生根据《周易本义》卷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及所附“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一段说明文字,发现了阴阳鱼太极图的精确画法,并发现此图与许多自然现象不谋而合[41]。这给我们以很大震动,也许其中自有一些深意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钱穆先生指出:“朱子论易图,实自有一番高情远寄,既非当时理学所能限,亦非后来考据所能拘。……朱子治易境界,实有超出宋儒义理清儒考据之外者。然朱子所论,亦非于义理有背,亦未尝置考据于不问,此正其不可及处。”[42]
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我们对待先哲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方式。简单否定和盲目推崇都是不负责任的轻浮态度,而平和公允则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易》之为用,无所不该
在提出“《易》本卜筮之书”、批评了偏执象数或义理的治《易》态度后,朱子又对绝大多数易学家解《易》时常见的拘执倾向进行了抨击。他认为,“《易》之为书,本为卜筮而作,然其义理精微,广大悉备,不可以一法论”[43],“《易》之卦爻,所以该尽天下之理。一爻不止于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备”,故治《易》千万“不要拘执著”[44],而应该“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说相碍”[45],要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他说:
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说。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46]
“《易》是个空底物事”,与他书不同,它是“未有是事,预先说是理,故包括得许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47]故“《易》之为用,无所不该”,学《易》、治《易》要灵活掌握,随缘应用,戒拘执偏颇,泥古不化。
在《易五赞·警学》中,朱子以更加精炼的语言表达了同一思想:
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执古御今,由静制动。洁静精微,是之谓《易》。体之在我,动有常吉。
这在《语类》卷67有详解。大意是,《易》理实有,《易》用无穷;理体存此,洁静精微;其用在人,随缘点化;体认此理,自然常吉。
朱子在这里所说“《易》之为书……义理精微,广大悉备”,“《易》之为用,无所不该”,与《周易·系辞》说的“《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系辞》是在颂扬《易经》,而朱子是为了批评易学史上拘执而不圆通的治《易》倾向。
令朱子深感惋惜的是,虽然程颐也明白“《易》不是限定底物”,他自己还说,“一爻当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当得三百八十四事?”[48],但到他解《易》时“却又拘了”[49]。以程子之博雅,治《易》也不免表现出拘执倾向,而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治《易》的不容易。
正因为治《易》如此艰难,所以朱子在谈到为学次第时,谆谆告诫后生学子,“《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50]然学者须明白,朱子此言是在讲为学次第,而并无否定《周易》之意。否则,他一生精研《周易》,他所说“圣人作《易》以立人极”[51],“《易》之为书……义理精微,广大悉备”,“《易》之为用,无所不该”,“熹近读《易》,觉有味”[52]……又怎么解释?他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53]
这是说,为学应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先看四书,再看《诗》《书》《礼》《乐》,最后看《春秋》及《易》;如果先看《易》,则极有可能事倍功半,如坠五里雾中,因为“《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不是启蒙读物。
朱子接着指出,《周易》“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读之”[54],学《易》须有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且须是“静定其心,自作主宰”[55],“以心验之,以身体之”[56],优游涵泳,默识心通,因为“道理须是与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57]他说:
《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只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58]
人能穷神则《易》之道在我矣,岂复别有《易》哉![59]
朱子在回答弟子“读《易》未能浃洽,何也?”的问题时,详细谈到了学《易》之法:
此须是此心虚明宁静,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罗得许多义理。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60]
可见,在朱子看来,学《易》的过程,应该是投身多彩生活、丰富自身阅历的过程,同时也应是加强自我修养、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唯有如此,方能以“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61]之心灵,和“虚灵洞彻”、悠然自得之胸次,默契于神妙玄奥之易理,游心于大美谨严之宇宙。这还不够,而应以悟得之易理“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62]
朱子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自豪地谈到了自己治《易》的深切体会:
玩之久熟,浃洽于心,则天地变化之神,阴阳消长之妙,自将了于心目之间,而其可惊可喜可笑可乐,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尽,偶得小诗以寄鄙怀,曰: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心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63]
此中真味,自非泥古不化或狂妄浅陋之徒所能侥幸得知;此种境界,须经无数熟读深思、勇猛精进的日日夜夜得来。为学当是如此,方是为学。学者当是如此,方为学者。
三.《易经》、《易传》、易学辨正
《易经》、《易传》本是二书,《易经》成于西周初叶,《易传》成于春秋战国,前后相距至少六百多年,且二者皆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人更多手、世历多时的集体作品。然自汉儒以传合经以来,经传不分、以传解经蔚然成风,几乎成为易学主流。更有学者非但经传不分,而且混淆《周易》与易学,致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
朱子对此有深刻了解,并提出了严肃批评,试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强调说:
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64]
这是因为,《易经》、《易传》和易学各自都蕴含着一个复杂社会背景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说“四圣一心”,皆为“因时立教”,易学家亦皆皓首穷经,多有心得,但是,由于每一作者或易学家都会受到其自身生活情境和天赋个性的影响,因此,“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65],故“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不能经传不分,混淆《周易》与易学,“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66]因此,朱子明确主张,应该严格区分《易经》、《易传》和各家易学。钱穆先生说:“朱子治易,分伏羲文王孔子为三,虽若犹拘旧说,要其分经分传各自推求,实为一极卓绝之见解。”[67]
朱子接着说:
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68]
朱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规定即是否定,说出来的越多,留给读者体会想象的可能性空间就越小,而关键是说出来的又几乎不可能达到“本义”,所以易学的发展史便是一个“本意浸失”的过程。这是必然的,但又只是问题一方面(另一方面即前面提及的“因时立教”)。而朱子在这里甚至对文王、孔子这样的传统圣人也敢于指摘,说明他不迷信权威而只崇尚真理,从而显示了特出的理论勇气和批判精神。作为朱子根本的学术立场,这种可贵的批判精神在其著述中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没有这种批判精神,也就没有朱子。后人对朱子的盲目崇拜则是与他本人的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的,足见他们只是想利用朱子,而并不想或并不能真正理解朱子。
与此同时,朱子又提出,应该充分肯定易学史上各家的独特价值。他说:
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69]
甚至对于在许多学者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卜筮之书,而朱子却仍然认为有“许多道理依旧在其间”。钱穆先生就此赞叹道:“朱子论易,不仅深切留意到无极太极先天后天之说,并以世俗如火珠林与灵棋课等与易相提并论,此其识解之宏通活泼,平实深允,洵可谓旷世无匹也。”[70]
朱伯崑先生指出:“他站在哲学史家的立场,强调还《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但不因此否认《易传》和历代易学解易的价值,这是朱熹研究《周易》经传的一大贡献。”[71]
朱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与其这种博大的胸怀和超凡的气度是分不开的。这正是,海纳百川,乃成其大。
四.一物各具一太极
按照一般的说法,朱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这样说并不错,但也不全对。应该说,在不同语境中,理、太极、道、心、天理等皆可以是最高范畴。
“太极是朱熹易学和哲学中的最高范畴。”[72]朱子对太极这一范畴给予了空前的重视。这可能与他极重视“易有太极”一节有关;也与他极推崇周子《太极图说》有关。
陈荣捷先生指出:“太极的概念对朱熹则是必不可少的。”[73]朱子赋予太极以至高无上的本体论地位和丰富精湛的思想内涵。在朱子那里,太极是宇宙“本然之妙”,“形而上之道”[74],是宇宙的本原,造化的源泉。他说:
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75]
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76]
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是个一而无对者”[77],是宇宙谨严秩序的终极根据。它是至高无上的,但却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恰恰相反,太极是超越而又内在的,它与宇宙万物是不离不杂、似二而一、似一而二的,它“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78],在万物之外而未尝不行乎万物之中,它的存在是离不开天地万物的,天地万物之中皆“自各全具一太极”。朱子就此指出: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79]
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
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80]
朱子以程颐“理一分殊”的命题,甚至借用佛教华严宗、禅宗“月印万川”的名喻,来说明其“一物各具一太极”的思想:
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81]
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82]
“一物各具一太极”,这一思想极为可贵:一方面,它充分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独特意义,和每个人生存的至上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在说,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内在于天地万物的,它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最终依据,是每个人生存的形上支柱。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其理论内部的必然要求,是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历史结晶;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朱子令人难以企及的形上学视野和深邃独到的人文关怀。
在朱子那里,太极作为宇宙本原,又具有其鲜明的道德属性。他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83]就是说,太极是使宇宙万物日益臻于完美至善的终极依据和动力。可见,朱子“这种学说是要为儒家传统的性善论进一步寻求本体论的支持。”[84]
不仅如此,因为“朱熹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他的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心与理一’的最高境界”[85],所以,在对太极进行了阐发后,朱子又对心这一范畴给予了充分关注,认为太极和理须由心来体认和确证,没有心,也就无所谓太极和理,提出“心包万理”,“心与理一”。这便是朱子的独到之处。他说: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86]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87]
在朱子看来,“万古长空一片心”,心是人亲证宇宙本体、体悟人生极境、洞察万化玄机、优游世间风云的先天灵明,是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理与天地万物不可或缺的体认者。没有“她”,谁去颂扬宇宙的谨严秩序、自然的壮丽神奇?谁去欣赏澄明的星空、浩瀚的海洋、圣洁的莲花、绮丽的朝霞?宇宙万物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提出“惟心无对”,心与理“本来贯通”,“理无心,则无着处”[88],“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89]。因此,刘述先先生说,“由于朱子思想内部的要求,必须把心当作他的哲学思想的枢纽点。”[90]朱子进一步说道:
人者天地之心。没这人时,天地便没人管。[91]
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于圣人。[92]
在这里,朱子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了人存在的至上价值,尤其高度称颂了圣人成己成物、“继天立极”[93]的神来智慧和卓越才能。这与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94]、“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95]的思想并无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种认为程朱与陆王水火不容的普遍说法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朱子之前,程颐已提出,“大而化,则己与理一,一则无己”[96],及“圣人与理为一”[97],李侗也有“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98]的命题。朱子继承了这些思想,也强调指出,为学的最高目标不是对于客观事物知识的了解,而是要达到“心与理一”、“默与道契”[99]、“与天为一”的理想人生境界。他说:
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天之未始不为人,而人之未始不为天也。[100]
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101]
圣人是人与法为一,己与天为一。[102]
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103]
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104]
虽然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105],“吾之心即天地之心”[106],但是,由于“此心多为物欲所陷了”[107],因而要达到“与天为一”的理想境界,关键是要“扫去气禀私欲,使胸次虚灵洞彻”[108],以体认“天地间非特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鸟兽草木之心”[109],自己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天地万物皆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生命存在,如此,即可达到“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110]、“见得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111]的高峰体验,臻于“此心廓然无一毫私意,直与天地同量”[112]的人生极境,从而,小我之有限、短暂,便自然跃迁为大我之无限、永恒,人的本质需要和至上价值因之得以实现。朱子及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也应从修养论这一视角去把握,才不至于有太大偏差。
朱子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仍然循循善诱地启发后学说:
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集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113]
就是说,为学须以“决定是要做圣贤”为“第一义,便渐渐有进步处”[114],然后专心攻读,丰富阅历,淡泊宁静,勇猛精进,而且“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115],及至真积力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16]。这样,便自然臻于“己与天为一”、“心与理一”的人生极境,因而能够以率真自然之天性,从容应对变化无穷之世事。
至此,朱子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深切感触,和对太极、理、心等范畴的独到阐发,成功建立了自己独步千古的形上学,因而“从世界观的高度,为儒家的理想人格、最高修养境界和伦理道德学说提供了理论的根据。”[117]
以上所述,只是朱子易学思想的大概轮廓,而其细部尚未论及。只此,朱子思想的博雅精湛已跃然纸上。当然,朱子易学中也有一些思想似欠斟酌,如“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以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一味崇信“天地自然之《易》”和伏羲之《易》,而认为自伏羲以下的易学发展是一个“本意浸失”的历史过程,等等。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但是,这也不应是我们苛责古人的理由。我们今天最紧迫的事情,决不是对古人吹毛求疵,而是虚心学习先哲的思想精华。
因此,面对朱子这样的思想巨人,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