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上古天真论 天人合一的四个层次
文/潘启明(辽宁)
我们追求天人合一,有四个层次。用今天的话讲,是同一、内化、认同、依从。
用《内经》的话讲,天人合一的人,有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高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内经·上古天真论》)
《庄子》分法大同小异,他把真人又分成天人和神人;把贤人叫做君子。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
真人是最高层次,天人完全一致,天地、阴阳、精气神、肌肉完全若一,天就是人,人就是天,完全不二,完全不分。至人则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将天内化。圣人则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是认同。贤人是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是依从。
孔子在《系辞》中虽然提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但却没有找到与天地如何同归,如何一致的办法。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效法天地。上察下察,远取近取,无非要像此(卦象、象数,象者像也),无非是效此(爻者,效也)。
文/潘启明(辽宁)
我们追求天人合一,有四个层次。用今天的话讲,是同一、内化、认同、依从。
用《内经》的话讲,天人合一的人,有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高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内经·上古天真论》)
《庄子》分法大同小异,他把真人又分成天人和神人;把贤人叫做君子。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
真人是最高层次,天人完全一致,天地、阴阳、精气神、肌肉完全若一,天就是人,人就是天,完全不二,完全不分。至人则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将天内化。圣人则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是认同。贤人是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是依从。
孔子在《系辞》中虽然提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但却没有找到与天地如何同归,如何一致的办法。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效法天地。上察下察,远取近取,无非要像此(卦象、象数,象者像也),无非是效此(爻者,效也)。
汉代董仲舒的功劳就是完整地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并且借用古已有之的“天子”之词,赋予皇权以天的代表。
《春秋繁露》共有六段涉及“天人”,其思想根本没有超过孔子的层次,也就是没有超过贤人的层次。
首先是孔子的办法,正名。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着,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五号自赞,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猕;无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诗曰:“维号斯言,有伦有迹。”此之谓也。
其次就是天人合一是最低层次的办法:法自然,效法天地。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故清溧之于岁也,若酸咸之于味也,仅有而已矣,圣人之治,亦从而然;天之少阴用于功,太阴用于空,人之少阴用于严,而太阴用于丧,丧亦空,空亦丧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是故天之行阴气也,少取以成秋,其余以归之冬;圣人之行阴气也,少取以立严,其余以归之丧,丧亦人之冬气。故人之太阴不用于刑而用于丧,天之太阴不用于物而用于空,空亦为丧,丧亦为空,其实一也,皆丧死亡之心也。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者,春秋讥也。
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若四时之条条然也。夫喜怒哀乐之止动也,此天之所为人性命者,临其时而欲发,其应亦天应也,与暖清寒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顺四时之名,实逆于天地之经,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气,使之郁滞,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天行谷朽寅而秋生麦,告除秽而继乏也,所以成功继乏以赡人也。天之生有大经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杀殛者,行急皆不待时也,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释,方求恶之时,见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杀人也,当生者曰生,当死者曰死,非杀物之义待四时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当行之理而必待四时也,此之谓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其宜直行而无郁滞一也,天终岁乃一遍此四者,而人主终日不知过此四之数,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谷也,除秽不待时,况秽人乎!
根本目的,还是维持社会的秩序
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今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见善者不能无好,见不善者不能无恶,好恶不能坚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名义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故曰:万物动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道也。
司马迁也没有超出孔子的取象比类层次。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心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此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列子》也提到天人,不过他把舜、禹、周公叫人,孔子桀纣以下就叫民的了。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乃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鮌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禹纂业事仇,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误,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鶡冠子》的层次比较高,涉及了异同的问题。
同而後可以见天,异而後可以见人,变而後可以见时,化而後可以见道。临利而後可以见信,临财而後可以见仁,临难而後可以见勇,临事而後可以见术数之士、九皇之制。主不虚王,臣不虚贵,阶级尊卑名号,自君吏民,次者无国,历宠历录,副所以付授。与天人相结连,钩考之具不备故也。下之所逜,上之可蔽,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缓则怠,急则困,见闲则以奇相御,人之情也。举以八极信焉,而弗信天之则也。差缪之闲言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毁於天珠蛤蠃蚌,虚于深渚,上下同离也。
《鶡冠子》的认为天是神,地是形。
庞子问鶡冠子曰:“圣与神谋,道与人成,愿闻度神虑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湿,神湿则天不生水。音□故声倒则形燥,形燥则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济济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贤不肖殊能,故上圣不可乱也,下愚不可辩也。阴阳者,气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圣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时之正也。故一义失此,万或乱彼,所失甚少,所败甚众,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膞膞之士之谓地也。所谓天者,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所谓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音者,其谋也;声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声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调则生理修,夫生生而倍其本则德专。己知无道,上乱天文,下灭地理,中绝人和。治渐终始,故听而无闻,视而无见。白昼而闇,有义而失谥,失谥而惑,责人所无,必人所不及。相史於既而不尽其爱,相区於成而不索其实。虚名相高,精白为黑,动静组转,神绝复逆,经气不类,形离正名,五气失端,四时不成。过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将极,驱驰索祸,开门逃福,贤良为笑,愚者为国,天咎先见,菑害并杂,人孰兆生,孰知其极!见日月者不为明,闻雷霆者不为聪,事至而议者不能使变无生。故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圣王独见,故主官以授,长者在内,和者在外。夫长者之为官也,在内则正义,在外则固守,用法则平法。人本无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内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败是,令不伤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谨,胥靡得以全。神备於心,道备於形,人以成则,士以为绳。列时第气,以授当名,故法错而阴阳调。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骐麟者,元枵之兽,阴之精也;万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其精毕至。”
人世间所有学问,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孔子的学说,是从人出发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孔子主张身、家、乡、邦、国、天下的次序。
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这样复杂。既然极终目的是人,为什么不从人开始,而且紧抓不放?
我喜欢老庄。老子始终把和、返、一当做最重要的东西。他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他最根本的办法,始终是精神内守,虚其心实其腹,不争无为。他看到了人与天的区别,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主张人天要统一,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他给出的办法,就是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贵、不自生、不自为大,就是无欲、无为、不争、不盈、下、朴、慈、俭、守雌、昏愚顽鄙、婴儿赤子。完全自然,没有多余的东西,纯粹,归一,归于自然,自然而然。归一才能知和,归一才能知常。
庄子非常明确地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办法,就是忘人
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liáng)乎人者,唯全人能之。虽虫能虫,虽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适羿,羿必得之,或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者拸(音chǐ)画,外非誉也。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夫复謵(音xí)不馈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庄子·庚桑楚》)
《庄子》讲,“天在内,人在外”。这是最高的层次。没有内化的经历,不懂得共性寄于个性之中,不了解“天”无处不在,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是理解不了“天在内,人在外”的。而对“何谓天?何谓人?”的回答,则更是痛快淋漓。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踯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周易参同契》说,“收敛真精”,“凝神以成躯”,“含精抱神”,“凝精流形”。完全道出了天人合一的办法。“宣耀精神”,从《庄子》的“天在内,人在外”的角度讲,也可以说宇宙意识在最内,其次是人的潜意识,即精,再次是人的显意识,或神,最外是形,是人。三家归一,五家归一,就是一个气,一个意(忆),一个能量。得到精气神的真蒂,就得到了天人合一的真蒂。

汉代董仲舒的功劳就是完整地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并且借用古已有之的“天子”之词,赋予皇权以天的代表。
《春秋繁露》共有六段涉及“天人”,其思想根本没有超过孔子的层次,也就是没有超过贤人的层次。
首先是孔子的办法,正名。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着,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五号自赞,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猕;无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诗曰:“维号斯言,有伦有迹。”此之谓也。
其次就是天人合一是最低层次的办法:法自然,效法天地。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故清溧之于岁也,若酸咸之于味也,仅有而已矣,圣人之治,亦从而然;天之少阴用于功,太阴用于空,人之少阴用于严,而太阴用于丧,丧亦空,空亦丧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是故天之行阴气也,少取以成秋,其余以归之冬;圣人之行阴气也,少取以立严,其余以归之丧,丧亦人之冬气。故人之太阴不用于刑而用于丧,天之太阴不用于物而用于空,空亦为丧,丧亦为空,其实一也,皆丧死亡之心也。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者,春秋讥也。
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若四时之条条然也。夫喜怒哀乐之止动也,此天之所为人性命者,临其时而欲发,其应亦天应也,与暖清寒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顺四时之名,实逆于天地之经,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气,使之郁滞,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天行谷朽寅而秋生麦,告除秽而继乏也,所以成功继乏以赡人也。天之生有大经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杀殛者,行急皆不待时也,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释,方求恶之时,见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杀人也,当生者曰生,当死者曰死,非杀物之义待四时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当行之理而必待四时也,此之谓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其宜直行而无郁滞一也,天终岁乃一遍此四者,而人主终日不知过此四之数,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谷也,除秽不待时,况秽人乎!
根本目的,还是维持社会的秩序
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今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见善者不能无好,见不善者不能无恶,好恶不能坚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名义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故曰:万物动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道也。
司马迁也没有超出孔子的取象比类层次。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心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此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列子》也提到天人,不过他把舜、禹、周公叫人,孔子桀纣以下就叫民的了。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乃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鮌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禹纂业事仇,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误,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鶡冠子》的层次比较高,涉及了异同的问题。
同而後可以见天,异而後可以见人,变而後可以见时,化而後可以见道。临利而後可以见信,临财而後可以见仁,临难而後可以见勇,临事而後可以见术数之士、九皇之制。主不虚王,臣不虚贵,阶级尊卑名号,自君吏民,次者无国,历宠历录,副所以付授。与天人相结连,钩考之具不备故也。下之所逜,上之可蔽,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缓则怠,急则困,见闲则以奇相御,人之情也。举以八极信焉,而弗信天之则也。差缪之闲言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毁於天珠蛤蠃蚌,虚于深渚,上下同离也。
《鶡冠子》的认为天是神,地是形。
庞子问鶡冠子曰:“圣与神谋,道与人成,愿闻度神虑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湿,神湿则天不生水。音□故声倒则形燥,形燥则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济济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贤不肖殊能,故上圣不可乱也,下愚不可辩也。阴阳者,气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圣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时之正也。故一义失此,万或乱彼,所失甚少,所败甚众,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膞膞之士之谓地也。所谓天者,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所谓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音者,其谋也;声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声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调则生理修,夫生生而倍其本则德专。己知无道,上乱天文,下灭地理,中绝人和。治渐终始,故听而无闻,视而无见。白昼而闇,有义而失谥,失谥而惑,责人所无,必人所不及。相史於既而不尽其爱,相区於成而不索其实。虚名相高,精白为黑,动静组转,神绝复逆,经气不类,形离正名,五气失端,四时不成。过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将极,驱驰索祸,开门逃福,贤良为笑,愚者为国,天咎先见,菑害并杂,人孰兆生,孰知其极!见日月者不为明,闻雷霆者不为聪,事至而议者不能使变无生。故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圣王独见,故主官以授,长者在内,和者在外。夫长者之为官也,在内则正义,在外则固守,用法则平法。人本无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内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败是,令不伤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谨,胥靡得以全。神备於心,道备於形,人以成则,士以为绳。列时第气,以授当名,故法错而阴阳调。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骐麟者,元枵之兽,阴之精也;万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其精毕至。”
人世间所有学问,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孔子的学说,是从人出发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孔子主张身、家、乡、邦、国、天下的次序。
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这样复杂。既然极终目的是人,为什么不从人开始,而且紧抓不放?
我喜欢老庄。老子始终把和、返、一当做最重要的东西。他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他最根本的办法,始终是精神内守,虚其心实其腹,不争无为。他看到了人与天的区别,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主张人天要统一,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他给出的办法,就是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贵、不自生、不自为大,就是无欲、无为、不争、不盈、下、朴、慈、俭、守雌、昏愚顽鄙、婴儿赤子。完全自然,没有多余的东西,纯粹,归一,归于自然,自然而然。归一才能知和,归一才能知常。
庄子非常明确地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办法,就是忘人
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liáng)乎人者,唯全人能之。虽虫能虫,虽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适羿,羿必得之,或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者拸(音chǐ)画,外非誉也。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夫复謵(音xí)不馈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庄子·庚桑楚》)
《庄子》讲,“天在内,人在外”。这是最高的层次。没有内化的经历,不懂得共性寄于个性之中,不了解“天”无处不在,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是理解不了“天在内,人在外”的。而对“何谓天?何谓人?”的回答,则更是痛快淋漓。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踯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周易参同契》说,“收敛真精”,“凝神以成躯”,“含精抱神”,“凝精流形”。完全道出了天人合一的办法。“宣耀精神”,从《庄子》的“天在内,人在外”的角度讲,也可以说宇宙意识在最内,其次是人的潜意识,即精,再次是人的显意识,或神,最外是形,是人。三家归一,五家归一,就是一个气,一个意(忆),一个能量。得到精气神的真蒂,就得到了天人合一的真蒂。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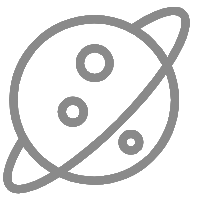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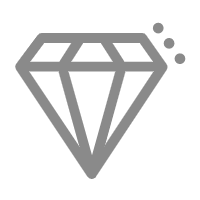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