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
台靜農序
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居士。山陰人,其先世為蜀之劍州人,故《自為墓誌銘》稱「蜀人張岱」。宗子的家世,頗為顯貴的。高祖天複嘉靖廿六年進士,官至太僕卿;曾祖元汴,隆慶五年狀元,官至左諭德侍經筵;祖汝霖,萬歷二十三年進士,視學黔中時,得士最多,楊文籩梅豸俱出他的門下,當時黔人謂「三百年來無此提學」;父耀芳,為魯藩長史司右長史,魯王好神仙,他卻精導引術,君臣之間,甚是契合。(以上俱見《瑯環文集》卷四家傳)宗子之能享受那樣豪華的生活,如《夢憶》中所寫的,正因其生長於這樣家庭的關系。
宗子《自為墓誌銘》說生於萬歷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禎甲申明亡時,他已四十八歲了。他的死年有兩說:邵廷采的《逸民傳》,說活到七十多歲,而徐鼐的《小腆記傳》補遺說活到八十八歲(一六八四)。大概後說是可靠的,因《蝶庵題象》有「八十一年,窮愁桌犖」之語,(《文集》卷五)這顯然不止於七十餘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開明史館,毛奇齡以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當時寄信給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藍本(《西河全集》書四)。開明史館這年,他已八十三了,記齡的信可能就寫在這一年,也可能在這一年以後。足見說他活到八十八歲,一定有所根據的。
據此知宗子國亡以後,在滿清統治下,還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麼,他的生平可以甲申為限,劃作兩個階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極為豪侈,而態度是極為放縱的。《自為墓誌銘》雲:「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譎謔,書囊詩魔。」這是他真實的自白,而《夢憶》一書中所記的又是更加具體的事實。
國亡後的生活,則大大不同了。《墓誌》雲:「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雖然,這樣的貧乏在他是甘心的。《遺民傳》雲:「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於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夢憶》自序亦雲:「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駭駭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間。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一向生活於華貴的家庭,而又沉溺於聲色狗馬之好,一旦國亡,不乞求保全,如錢謙益阮大鋮一類人的行為;只將舊有的一切一切,當作昨夜的一場好夢,獨守著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紀傳,寧讓人們將他當作毒藥,當作猛獸,卻沒有甚麼怨悔。大概一個人能將寂寞與繁華看做沒有兩樣,才能耐寂寞而不熱衷,處繁華而不沒落,劉越石文文山便是這等人,張宗子又何嘗不是這等人?錢謙益阮大鋮享受的生活,張宗子享受過,而張宗子的情操,錢阮輩卻沒有。
一場熱鬧的夢,醒過來時,總想將虛幻變為實有。於是而有《夢憶》之作。也許明朝不亡,他不會為珍惜眼前生活而著筆;即使著筆,也許不免鋪張豪華,點綴承平,而不會有《夢憶》中的種種境界。至於《夢憶》文章的高處,是無從說出的,如看雪個和瞎尊者的畫,總覺水墨滃鬱中,有一種悲涼的意味,卻又捉摸不著。余澹心的《板橋雜記》,也有同樣的手法,但清麗有餘,而冷雋沉重不足。
宗子的詩文,是受徐文長的影響,而宗子來得深刻,這因為他是亡國的逸民的關系。文長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傳雲:「徐文長以殺後妻下獄,曾祖百計出之,在文長有不能知之者。」當時他的祖父還是小孩子,曾去獄中看文長,「見囊盛所卓械懸壁,戲曰:『此先生無弦琴耶?』文長摩大父頂曰:『齒牙何利!』」這樣惡謔,大概對徐文長是合適的,在別人我想可受不了,但於此可以看出他們張家不是道學的家庭。宗子年少時,曾從事搜集過文長的佚文,以所收頗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謔庵為之刪削。(見《文集‧與王謔庵書》)但四庫總目著錄《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雲「為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許藉以表彰其先德罷。此書末卷所載優人謔、吃酸梨偈、放鷂圖、對聯、燈謎諸作,《提要》謂「鄙俚猥雜,豈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別集類存目五)然宗子卻雲:「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銘抄自序)。足見宗子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而與提要作者的頭腦不是同一的範疇。徐文長文章的風格,傳統的文學觀念者,批評為鄙俗纖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長唾棄七子,自成風格;袁宏道謂其:「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徐文長傳》),不是無見之言。以張宗子的天才學力,而猶追逐於文長的,固由文長在當時文學上造成的清明風氣足以影響他,而同是不羈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長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無所薰染罷?
宗子不僅長於文學,且長於史學,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過生命相依的《石匱書》。是書寫了幾五十年才脫稿(《文集》卷一《石匱書自序》),脫稿後猶時加刪改,故與李硯翁書有「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之語。(《文集》卷四)順治年間浙江學使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購買《石匱書》,宗子慨然予之。(思複堂《逸民傳》)至於毛奇齡寄書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按《逸民傳‧談遷傳》雲:「名季廒史雖多,而心思陋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俱有本末,谷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於此可知《石匱書》與《明史紀事本末》的關系。雖然,《石匱書》稿本並未因曾與谷應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時,聞朱逖先先生藏有此書,為海內孤本雲。
關於《夢憶》的版本,有硯雲甲編本一卷,王文誥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後因雕板失去,重刻為巾箱本,有王文誥見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譚複堂日記》卷三稱之為王見大本。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粵雅堂叢書》者,即據王本。頃開明書店經理劉甫琴先生來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書,愛好者甚多,今取粵雅堂本標點重印,屬為一序,俾讀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雜寫此。
台靜農序於台北龍坡裡之歇腳庵
湖心亭看雪 中国古籍全录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沅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粵雅堂本《陶庵夢憶》卷三)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明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杉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幾暖爐,茶鐺旋煮,素瓷淨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裡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複整妝,湖複頯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裡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粵雅堂本《陶庵夢憶》卷七)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發,然又找截干淨,並不嘮叨。誖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吒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閒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瓷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陶庵夢憶》卷五)
自為墓誌銘
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悲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干,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游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是能辨澠、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稱石公,即字石公。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擐(女字旁)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傒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生於萬歷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養於外大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宦兩廣,藏生黃丸盈數麓,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廖。六歲時,大父雨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為錢塘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塘縣裡打秋風。」眉公大笑,起躍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余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
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發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為之。甫構思,覺人與文俱不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曾營生壙於項王裡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冢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裡也。明年,年躋七十,死與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書。
銘曰:窮石崇,斗金石。盲卞和,獻荊玉。老廉頗,戰涿鹿。贗龍門,開史局。饞東坡,餓孤竹。五羖大夫,焉能自鬻?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終曲。
《西湖夢尋》自序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及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如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安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溪,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於徐,唯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歲辛亥七月既望,古劍蝶庵老人張岱題。
明聖二湖 中国古籍全录
自馬臻開鑒湖,而由漢及唐,得名最早;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鑒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艷矣。至於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古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儒,常比西湖為美人,湘湖為隱士,鑒湖為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為處子,靦腆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鑒湖為名門閨淑,可飲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為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媟褻,故人人得而艷羨;人人得而艷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哄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清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游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巘古梅,何遜煙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空濛,何遜晴光灩瀲?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即湖上四賢,余亦曰:「樂天之曠達,固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於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間措大,何得易言西湖!(明聖湖為西湖別名,《西湖游覽誌》:「明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西湖原有外湖、裡湖之別,又稱二湖。)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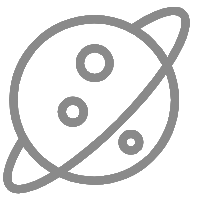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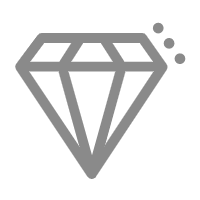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