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女孩的故事
梦游女孩的故事就让我假设它发生在纽约吧。
纽约这个城市只是以城市这个概念存在着,许多人喜欢它,也有许多人憎恶它。当然结果是一样的,你可以喜欢或者憎恶某个既存的概念,你却无法改变它。我很喜欢纽约。
至于梦游女孩喜欢纽约与否呢?这恐怕是她自己也是无法回答的。
梦游女孩发觉自己有梦游的毛病是在一个昏暗的清晨。
地铁列车从木窗外经过,轰隆隆的。整座屋子都在剧烈地摇晃着。
对面屋子的外墙上是许多扭曲肮脏的涂鸦。隔壁传来福州大嫂尖锐的声音。她发现自己的床头多了一束沾染着星点新鲜黑泥的野菊花,规规矩矩地插在玻璃杯子里。
她轻轻地凑了过去,抚摸着花瓣。笑了。那可是她在梦中拾起的野菊花呀。她是如此清晰地回忆着。
梦游女孩也是有名字的,福州大嫂称呼她叫小丽。糕点店的广东老板管她叫张力。渐渐地,她就无所谓了。白天她坐在阴沉沉的龙凤饼家里面,生意很差,老板基本上不来的。后面干活的阿发和阿雄抽着烟,把许多焦黄的饼搬到柜台前面。偶而有好奇的本地人经过,拿着小巧的照相机对着铺面拍个不停,这时候梦游女孩总会不由自主地微笑。在远去的相机里,她模糊地感觉着自己的存在。
“梦游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悄悄地问她。
她瘦弱的眼神向上延伸着,嘴角于是浮现着微笑。
我开始了漫无边际的想象。远处的女孩暖暖地微闭着双眼,恬笑着从流金一般的岁月深处向我走来。
梦游女孩从来没有踏出过唐人街。她不懂英语,她也不懂广东话。
渐渐地,她就无所谓了。这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她说话的机会。
下班后,她从熙熙攘攘的东百老汇大街上走过。没有人可以听见她心里歇斯底里的尖叫。刚刚进入纽约的那个月,她每天都被这种鬼魅般的尖叫撕扯着。然后也只是一刹那的功夫,一切就归于安静了。
“然后我就开始梦游了。”她的手指带着点黄,很瘦,有了一些和年龄不大相称的皱纹。
晚霞铺天盖地而来,我和她坐在东河的河边,远处是巍峨的曼哈顿大桥,无数寂静而且陌生的房子亮起了灯,天空中缓慢地行进着无数斑驳陆离的云。风景这东西依旧心不在焉地存在着。
我第一次观看那盒录像带的时候很吃惊,因为梦游中的她居然在开车。还听见她很爽朗的笑。她那双黄而瘦的手熟练地把握着方向盘。路笔直而且长。前方车灯晃不着的地方仿佛有惊慌失措的鹿。
“你会开车?”
“不会。”她也是一脸愕然地瞧着不停晃动的画面。
当然梦中的一切都是另当别论的。就象那双很白很干净的手突如其来地出现一般。画面上的手顽皮地晃动着。但依旧没有人说话。那应该是一双男人的手吧。梦游女孩长久地把这个镜头定格。不说话。
“我一定握过那双手的。”梦游女孩很肯定地对我说。“我甚至记得那手掌上如溪水一般蜿蜒的纹理呀。”
梦游女孩继续恬静地行走在黑暗肮脏的纽约街头,头顶上行进的月散发着不可思议的白光,一切曾经确实的存在都在不知不觉中扭曲了,模糊了,慢慢地也就碎开去了。
但她还是如此真切地回忆着,那双手,那双干净而且洁白的手。
第一次,梦游女孩在梦中拾起了野菊花。
但当事情慢慢发展下去的时候,她的房间就显得过于狭小了。
她从外面搬回来了许多的东西。当一天早上起来,她发觉面前居然屹立着地铁站前面的巨型指示牌的时候,她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
“也许下次我会把孔子像也搬回来吧。”
下班的途中,她很认真地围绕着路口的孔子像转了许多圈。在确定它真的很重很稳很慈祥之后,她才稍感安心地回家。
梦游女孩决定不再睡觉了,至少尝试不在晚上睡觉吧。
于是第二天中午她午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阿发和阿雄的嘴里都被均匀地塞了四个刚出炉的黄皮蛋挞,拥挤在墙的一角一脸无可奈何地看着她。
她第一次地,不在梦中,也开心地笑了。笑得象一只名副其实的小母鸡。她甚至开始喜欢梦游了,特别是在这座无可名状的城市里。
我第二次观看那盒录像带的时候,嘴巴上的惊讶也辽阔得可以塞得下四个黄皮蛋挞。她明显是在纽约大学附近一家不知名的小剧院里,旁边是许多发型古怪,呼吸沉重的男人。霉臭的味道在不停呻吟的画面前面升腾。
“你还去看三级片?”
“不知道。”她继续一脸愕然地瞧着。
她再次看见了那双很干净而且洁白的手,上面遍布着如溪流一般蜿蜒的纹理。
当然梦中的一切都应该是另当别论的
“我一定握过那双手的。”梦游女孩很肯定地对我说。
“我甚至记得那手掌上如溪水一般蜿蜒的纹理。”
当终于清晰地回忆起那股温存的感觉的时候,梦游女孩怔怔地坐在了床边。
“我知道我在梦中握过一些什么的,就那么很轻很轻地握住了。”
她那浅浅细细的笑容在午后的阳光下,仿佛只是隔了一层毛玻璃,柔柔地就化了开去,暖洋洋地荡出去好远。
在纽约这块儿地上是没有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你是说在梦中,或者说在梦游的时候,有人一直握着你的手吗?”
“难道不是吗?”
这一切都发生在梦游已经成为了习惯的时候,也是晚归的福州大嫂看见她足不沾地般飘下楼梯而去也不再需要尖叫的时候。
那位叫张力的梦游女孩决定要买一部摄影机了,很微型那种。
我承认这是极其异想天开的主意,但在纽约这块地上是没有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我第三次观看那盒录像带的时候,她却是在地下。
依旧可以听见她很爽朗的笑。四周光晃晃的,有许多精亮的细柱子。
他们在地铁列车里,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腰部线条微妙的背影。一个男孩的背影,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的。
虽然男孩曾经很刻意地回避着镜头。但最后我还是看见了他很瘦潇的脸,是个颈部精致的西班牙男孩,许多地中海的痕迹还没有风化贻尽,表情就象他微微卷曲的头发一般溢着点俏俏的慵懒。
这一切是真实的吗?但所谓真实又是什么概念呢?
梦是真实的吗?梦游女孩在睡前很认真地把摄影机捆绑在胸前。
她安静地平躺在浅蓝色的床单上,风由远而近地穿堂而过,然后带着些不甘心地拍打了一下布满锈迹的走火铁梯。“咣”的一声响,声音仿佛来自家乡。梦游女孩愣愣地听着,然后微笑,也就痴过去了。
外面的街道有夜归的餐馆工人在唠唠叨叨地走过,许多琐碎的声响轻巧地滑了一下也就没有了。月色如水。那晚开始,她连续地失眠了。
她于是有了一个更疯狂的主意。她决定假装梦游去见见那个西班牙男孩。
“假装梦游?”
“对啊,我很想在清醒的情形下看看他。”
她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微微地闭着眼睛,睫毛颤抖,非常清冷的夜迫不及待地把她拥抱着,
她有些手足无措地立在街角,白天曾经熟悉的街道在夜的抚弄下已经面目全非了。她的心跳好快,
仿佛只是一位无意闯入寂寞后花园的忧郁女孩。
然后,西班牙男孩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轻轻地拾起她的左手,在那黄而且有些瘦的手背印了一
吻。他们执着手,也就融进了某种不可思议的概念里面去了。
帝国大厦饱满的尖顶晃动着一些暧昧甚至妖媚的蓝光。格林威治村的圆石地面光滑得连最吊诡
的欲望,自怜以及感伤都无法驻足,长岛酒吧中的聚集者们惊呼着仰望,纽约的天空散布着一片难
得的干净,中央公园的深处有空洞的长笛声,还有如连射的勃朗宁手枪一般清脆干爽的马蹄声。
梦游女孩张力和西班牙男孩并肩坐在马车上,她的手心不停地渗着汗,西班牙男孩一直没有说
话,他很安静,甚至连脸上微髯也一动不动,偶而他也会侧头看一眼梦游女孩吧,刀削一般的嘴唇
紧紧地闭着,眼神温柔。他那干净而且洁白的手掌上有着如溪水一般蜿蜒的纹理。
“你们就一直坐着马车在中央公园里面游荡?”
“是啊,后来他就送我回家了。”
女孩从微闭的眼间偷偷看出去,四周的林子黑悠悠的,有些精灵们嘤嘤的哭声传出来,不知名
的大鸟扇着黑色的羽翼飞过。空中没有月亮,但公园里面还是很亮,黄绿相间的树叶边缘镀了浅浅
的一层与岁月无关的银灰色。
“后来呢?”
“后来,我就没有再梦游了。”
梦游女孩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那晚的录像带。
那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摄影机就丢失了,她醒来的时候发现门前剩下了这盒录像带,孤零零地
躺在漆痕斑斑的地面上,游离于一切记忆之外而遗世孑立着。
西班牙男孩在摄像机面前正襟而坐,背景由于焦距没有调好吧,只有一块接一块的黑色和黄色
在衔接着。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你没有去探究他说了一些什么吗?”
“没有。其实我是不敢去了解他说了一些的,一直,我就觉得他只适合生存在我梦里的。那晚
,我假装梦游看见他之后,我就更清楚了,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不可以存在的。”
这是我认识梦游女孩以来她说得最长的一句话了。
“为什么呢?”
梦游女孩不说话了。她微笑着附下身子,看,岸边开满了许多野菊花。风大了一些,野菊花随
风摇弋着,它们都应该有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吧,但既然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那么继续漫不经心地
盛放也许是最适合他们的存在方式了。
女孩张力拾起了一朵野菊花,她轻轻地凑了过去,抚摸着花瓣。笑了。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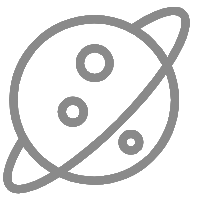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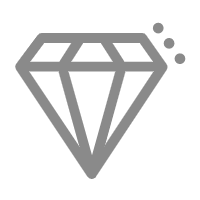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