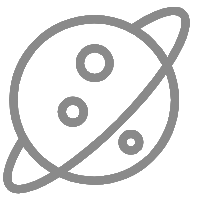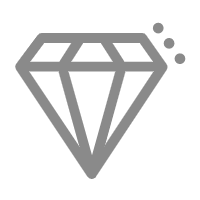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ARTX.CN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六篇。至孔子时,礼文废阙,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这八方面,统括礼之大体,故孔子手定此十七篇以为教本。所谓《逸礼》,即令非伪,亦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这便涉及到《仪礼》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关于《仪礼》的作者问题,传统有三种说法,一说周公作,一说孔子作,一说周公作孔子删定,清人又有疑《仪礼》为伪书者。清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认为《仪礼》是“真书杂以伪者”(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4页)。顾栋高作《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则直疑《仪礼》为汉儒所缀辑。
伪书说不能成立。汉代《仪礼》的传授,自汉初高堂生以下五家(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不绝如缕,条理清楚。先秦典籍,如《左传》、《论》、《孟》,对《仪礼》所记礼仪节次,多所称引,都可为证。此点清人胡培翚《仪礼非后人伪撰辨》论之甚详。周公作《仪礼》之说亦不可据信。盖礼仪乃因俗立制,有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大戴礼记·礼三本》所谓“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讲的正是这个道理。邵懿辰《礼经通论》说:“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这种看法是对的。但若依此说,《仪礼》作为周礼,便不能遽尔完成于周初的周公。梁启超说:“《仪礼》。。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0页)此说当近乎历史实际。
关于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此处“礼记”,即指《仪礼》。《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按史公说法,孔子对《仪礼》,是“修起”,而不是“作”。“修起”,就是整理修复,免于澌灭。孔子生当春秋“礼坏乐崩”之世,对三代之礼,特别是周礼,上下搜讨,力求其重建,此点史有明文,不必复赘。
《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檀弓》篇亦记载此事。这是孔子“修起”《仪礼》的确证。《礼记·礼运》记孔子答弟子子游问礼语云:“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夫礼。。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邵懿辰认为射御之“御”为“乡”字之讹。孔子关于礼之所论列,正是《仪礼》十七篇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说,《仪礼》一书的内容,非一时一世而作,大致形成于西周末春秋初,孔子编定为十七篇,使周代礼仪之大体,得以保存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