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逐渐开始会通,因西方逻辑以及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清代沈孝瞻在深入探究传统命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命学逻辑化的尝试,这是《子平真诠》论命思路的文化根基,这种建构理性与中国传统的体用观念产生了契合,从而在传统体用逻辑的框架下,重点对“用”方进行系统的梳理,分类,用各种格局来对体-用这种框架里的“用”进行研究。从而以用来彰显日主这个“体”在整个八字中的状态,也即日主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所以格局其实是对日主生存的客观环境的一种考量。这是沈孝瞻《子平真诠》体系的论证基础,也是研究《子平真诠》一书的思维起点。
当前研究命学之人,有格局传统、盲派宾主、新派简法等等,各自有各自体系,章法,但唯日主为论命主体的思维勿论,诸法统一,未见分歧,虽本人有年命,月命、时命法等创新,但理论目前依然建构中,毕竟不成熟,在此不论。对于格局传统,日元为主的论法,这是诸多典籍的界定,无从非议。但近来命学研究者似乎对日元本身关注要么太多,要么太少。月令格局研究者,论命以月令为重心,凡命月令定格无可非议,然有甚者居然连日主本身旺衰都不顾,日元本身属性都不顾,过于偏激。亦有旺衰论命者,只求平衡,而对格局则马虎对待,凡八字中对日元有用,则为用;对日元无用则为忌;不分月时,不看年日,主次不分,体用不清,亦属偏颇;其实,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诸多研究者对命学的体系不熟,往往管中窥豹,不能见微知著。
《子平真诠》的核心思维上文谈过,依然是体用之道,未能免矣。真诠的行文思路,首论天干地支,次论阴阳,然后谈十干配合性情以及十干之旺衰;随后才是论用神。以及用神相关的变化,取法,配合,用神高低,格局层次,成格破格变格,行运变化等等。这种行文思路,不难看出,同其他命学著作思路一样,从最基础的干支,阴阳以及干支属性、旺衰出发,随后才能有各种组合,框架,搭配;而这些随后的搭配,组合,格局框架,用神都是对十干的一种“用”的概念。论命的中心依然在于日元这个“体”;诚如第四节《论十干配合性情》一章论到“如甲用辛官,透丙作合,而官非其官;甲用癸印,透戊作合,而印非其印”,中心点在“甲木”,至于官也好,印也好,都是以甲为体的中心之下的“用”的层面。再如《论用神》一章,开篇即论“八字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八字的用神,整体上理解可以考虑为对八字有用的神;那么是谁的八字,就是对谁有用;那么以日元当成八字的属主,主人;那么八字中对日元有用的,就是用神,但是八字中未必一个用神,如同一个人有多重喜好,或者很多东西对一个人都有好的作用,那么用神就未必是唯一的。但沈孝瞻认为,用神要“专求月令”,实际上有个逻辑转换没有明白表达出来:那就是对于日主而言,八字中对日主影响最大的就是月令,这是第一个逻辑层次;第二个逻辑层次,沈孝瞻认为的“用神”并非我们通常简单考虑的“有用之神”或者说“发挥好的作用的神”,沈孝瞻认为的“用神”其实就是“日主能使用的十神”,他这个意义上的“用神”没有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字(沈孝瞻主要指的是月令)对日主是好,是坏,在第一个逻辑层次选取月令这个字的时候,是没有定论的,可好,亦可坏,好坏在于两个逻辑层次:
第一个逻辑层次是:对照日元来讲,有十神的吉凶划分:财官印食为吉,杀伤劫刃为凶。但是这种吉凶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大的框架上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后文沈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勿论对日元是吉是凶,只要配合得好,都可对日主产生好的作用。这种吉凶的划分,对日主来说其决定意义不大,这种划分其实是为了后续的“相神”的介入做出的铺垫而已。也就是说,先有了十神的吉神凶神的划分,才有如何选择“使用”的方式的考虑。于是吉神居月令,则顺用—辅助性的,保护性的使用;凶神居月令则控制性,抑制性的使用。那么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沈孝瞻的“用神”没有吉凶的本质,或者说其吉凶的本质在于“相神”的配合,在于如何构筑一个客观的和谐的环境而已,在于其整体上对日主发挥的作用。是官还是杀,在本身上没有任何吉凶,对日主不会产生明显的吉凶意义,只有其与相神的配合,以及其他的配合才最终决定日主乃至命局的吉凶。
那么其思维的逻辑就显而易见:日主首先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八字的中心,一个体,一个主体,一个核心。这是我们要分析命局的首先切入点。就如同一个人穿什么衣服,首先我们要考察这个人,衣服本身其实无所谓美丑,关键在于这个衣服穿在什么人身上,这个衣服只有搭配在一个具体人身上才有其意义,衣服是用来修饰人,打扮人,甚至定义人,穿警服未必绝对是警察,但是大多数是警察,这个毫无疑问,穿童装未必绝对是小孩,但是大多穿童装都是小孩。穿裙子未必是女人,但是大多穿裙子的都是女人。人才是主体,衣服是用来修饰人的客体。日主是八字的主体,格局是为日主所用的客体。那么沈孝瞻日元配月令,格局分焉的说法,改成月令配日元,则格局分焉似乎更为符合他的理论。这是第一个逻辑层次,必须确立日元作为主体,其次考察月令订立格局,那么这个格局完全可以假设性的抛开日元,作为来考察日元的一种客观环境;也就是说,格局实际上是对日元来修饰的一个衣服,一个论证的框架。但是很多人重视格局,却忽略了日主的中心地位,大致上可能是初学命理的时候,直接旺衰论命为格局论命者所诟病,但是这种诟病发挥得太极端,就最终因为诟病旺衰导致连日主为中心都在自己的潜意识里给忽略了。
在确立了日元---格局(体—用)这样一条模型之后,沈孝瞻分析的中心轻易的就转化了,这个论证的过程没有明说,基本一笔带过,而且这笔锋还显得非常晦涩,让我这个几百年后的易学后生来进行详细阐述。如何转化?就是直接将体用之道中的“用”作为考察的中心,也就是说将格局作为中心,直接把对日主进行描述的体系(除了日主以为的7个字)进行格局化的建构,整合,把除了日元以外的7个字作为考察的重点,但是这7个字又有一个主次之分,其中对日主影响最重要的首先就是月令,其次的就是与月令构成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就是格局,比如伤官生财;食神制杀;正官配印;伤官配印。。。。。。日元一直是排除在外的。
日元-----||伤官(月令)---其他干支(财)||----大运流年
日元-----||食神(月令)---其他干支(杀)||----大运流年
日元-----||正官(月令)---其他干支(印)||----大运流年
体--------用------大运流年
上图就基本廓清了鄙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子平真诠》重点考虑的是日主的客观环境,对日主本身的旺衰强弱的处理并非沈孝瞻考察的重点。他的格局也只是众多论命方法中的一种方式,除开日元之外其他7个字构成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他所认为的格局,这个格局是用来定义日主生存的环境的手段。所以他的用神其实是整个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沈孝瞻运用的是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模式,将日主以外的七个字构成一个类型,一个框架,来界定日主这个体而已。
那么在这个格局的内部,有不同的类型,从大的角度分类,有的类型是吉利的类型,也即成格的类型;有的类型是属于凶的类型或者不是很吉,也即破格的类型。直接说即是这种7个字的组合不太好,日主的生存环境不是很好,于是格局就存在高低,不同的组合配置导致了格局的高低之分。上文说了,格局是从日主出发研究八字的第二个逻辑:用的层面。那么对于这个“用”因为有配合,有组合。就存在用中之用。如伤官生财这种格局,伤官是格局之用,这个伤官虽然是凶神,但是并无实际吉凶意义,只是为了来定义使用的方式,才认为是凶神。当生财的时候,整体配合就是吉的,当没有财来配合,整体配合就是凶的了。也就是说,对于格局,其吉凶不能单独从月令是官,还是伤,这种吉凶上去定义,真正的吉凶要看其组合来界定。所以组合很重要,配合很重要。于是在确立了月令这个第一层次的用之后,还需要有配合这个用的东西,那就是沈孝瞻所论的“相神”概念了。相神才是八字取用的核心,“伤相神甚于伤用”。官格也好,杀格也好,重点在于相神如何发挥作用。当官未必吉,伤官未必就坏,全在“救应”二字,无非就是相神如何配合,干支如何搭配,除日元以外的7个字如何组合的问题了,力量轻重,位置摆放等等。
简单用图形表示:
第一逻辑:日元为体、格局为用
第二逻辑:格局为体、相神为用
第三逻辑:八字原局为体,大运流年为用。
第二逻辑从属于第一逻辑,第三逻辑从属于第一第二逻辑的综合。
第二逻辑第三逻辑最终都是为第一逻辑服务。日元才是八字的中心点。
(浙易)
声明:易德轩网部分内容来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以上内容,并不代表易德轩观点。

















 教学堂
教学堂  社区
社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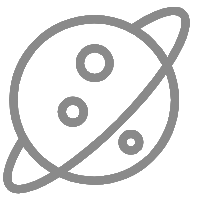 发现
发现 开运
开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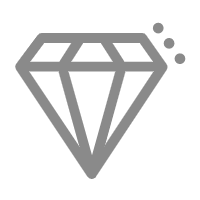 景观件
景观件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